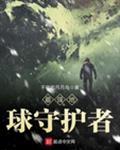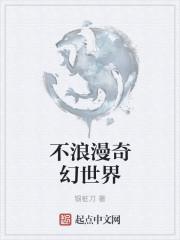笔趣阁>这也算修仙吗 > 第二十五章 观众里面有坏人(第4页)
第二十五章 观众里面有坏人(第4页)
她退出账号,删除所有本地缓存,拔掉SIM卡碾碎,将手机扔进炉膛点燃。
火焰升起时,她看见一只灰鸟落在银藤最高处,歪头看了她一眼,然后振翅飞走。
她背着包走出山谷,没有回头。
公路边上停着一辆旧巴士,司机是个戴斗笠的老妇,见她上来,也不问目的地,只递过一张泛黄的车票,上面印着一行褪色小字:
>“终点:无应之地”
林晚坐下,闭目养神。
车子启动,穿过雾霭弥漫的山道。途中经过一座废弃的数据塔,铁架上爬满藤蔓,顶端挂着一块破旧横幅,依稀可见曾写着“全球共感中枢?华南节点”,如今已被风雨撕扯得只剩两个字:
**“共……”**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老师教的一首童谣:
>小铃铛,不响才好,
>响了就会吵醒梦里人;
>梦里人,不说才好,
>说了就回不了门。
她轻轻哼了起来。
歌声很轻,轻得连自己都快听不见。
可就在那一刻,整辆车的乘客??那些一直低头沉默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全都缓缓抬起头,望向她,眼中闪着湿润的光。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鼓掌。
但他们都在听。
而这一次,林晚没有解释,没有记录,没有分析。
她只是继续哼着那首歌,直到巴士驶入晨光深处,直到歌声融进风里,直到所有人都忘记了这是谁的声音。
多年以后,有人在一本绝版心理学刊物上读到一篇匿名文章,署名为“一个曾经相信技术能治愈孤独的人”。
文中写道:
>“我们总以为倾听是为了被理解。
>可真正的疗愈,往往发生在‘被误解却仍被接纳’的瞬间。
>就像母亲明知你撒谎,却还是为你盖上被子;
>就像朋友听不懂你的痛苦,却愿意陪你坐到天亮。
>
>ECHO教会我们的最后一课是:
>最深刻的情感,从不需要精准传达。
>它只需要一个愿意沉默的耳朵,
>和一颗不怕说错话的心。”
文章末尾附有一张手绘插图:一口古井,井口结着蛛网,网上挂着一滴将坠未坠的露水,倒映着整片星空。
无人知晓作者是谁。
但在某些深夜,仍有少数人打开“哑河计划”的离线客户端,输入一句无人接收的话,然后静静等待72小时后系统自动焚毁记录的提示弹出。
他们并不期待回应。
他们只是坚持相信:
**有些声音,存在的意义,就是永不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