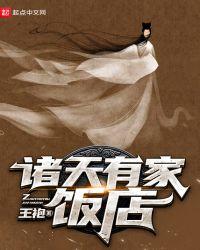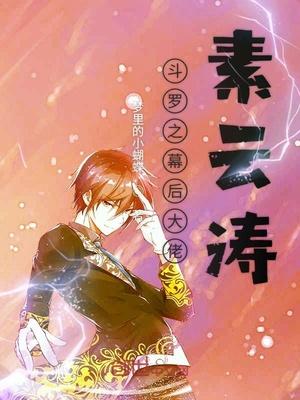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屁股坐正了吗?你就当导演 > 第175章 一拳拳倒一踢踢死彻底碾压(第2页)
第175章 一拳拳倒一踢踢死彻底碾压(第2页)
曹忠坐在角落,一直没说话。直到会议陷入僵局,他才开口:“各位老师,我想讲个故事。”
所有人看向他。
“去年冬天,我在漠河拍戏时认识了一个当地人,六十多岁,姓张。他儿子在北京送外卖,三年没回家。今年除夕夜,老张一个人包了饺子,拍了照片发给他。结果第二天早上,邻居发现他倒在厨房门口,手里攥着手机,最后一句话是‘爸给你留了韭菜馅的’。”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我没资格替他们决定什么叫‘合适’。我只知道,如果我们连这样的故事都不敢讲,那中国电影永远只能活在布景板后面。”
会议室安静了很久。
最终,主审委员叹了口气:“可以保留原结局。但建议在片尾加一段真实人物采访合集,平衡情绪。”
“没问题。”曹忠点头,“我已经录了二十多个普通人讲述自己的春运故事,最长的一个讲了四十分钟,讲他女儿走失又找回的经历。我会把它放在彩蛋位置。”
走出大楼时,天空又飘起了细雪。
韩三品迎上来:“怎么样?”
“过了。”曹忠呼出一口白气,“明天发布定档海报,大年初一全国上映。”
“王忠磊那边已经在动员水军准备刷差评了。”韩三品皱眉,“而且有几家院线跟我说,排片可能压到15%以下。”
“那就用数据打脸。”曹忠冷笑,“通知宣发团队,启动‘百城千村放映计划’??我们在一百个城市的一千个社区、工厂、工地、火车站设立流动放映点,免费首映《人在?途》。每场结束后,收集观众反馈,做成《中国人的回家路》纪录片短片,每天同步更新。”
“你是想绕过传统渠道?”
“不是绕过。”曹忠望着远处的央视大楼,“是重建规则。”
与此同时,远在洛杉矶的AMPAS总部,一份内部备忘录正在流传:
>**标题**:关于《我们生活在南京》参评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风险评估
>**摘要**:该片技术成就无可争议,人文表达极具感染力,且已形成全球舆论势能。若拒绝其入围,恐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压制的误解;若接受,则可能打破欧美主导的话语体系。建议采取“延迟策略”??通过学术讨论、评审流程细化等方式,延缓其影响力扩散。
而在东京,一位名叫佐藤健一的青年导演看完《人在?途》样片后,连夜写下一封公开信:
>“我曾以为日本的新浪潮才是亚洲电影的未来。但现在我才明白,真正的浪潮不在东京,不在首尔,而在北京,在那些愿意为普通人说话的镜头里。我请求加入‘亚洲青年电影联盟’,哪怕做一名助理导演,也想学习如何用电影对抗遗忘。”
这封信被翻译成中文后,迅速登上热搜。#亚洲电影需要新秩序#的话题阅读量突破十二亿。
春节临近,《人在?途》的宣传攻势全面展开。
地铁站、公交站、写字楼电梯屏,全是一张张真实的面孔:扛着蛇皮袋的父亲、抱着婴儿的母亲、戴着安全帽的工人……每个人眼中都有光,也有伤。
最震撼的是时代广场那一幕??当巨幕上出现老李站在废墟门前的画面时,无数华人驻足观看,有人当场落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撰文称:“这是继《寄生虫》之后,又一部迫使西方重新审视自身文明盲区的作品。”
大年初一凌晨,全国影院迎来罕见景象:零点场几乎全部满座。许多观众自带保温杯和泡面进场,像是完成某种仪式。
票房数据每十五分钟刷新一次:
>00:15,票房破亿
>02:30,累计4。7亿
>08:00,单日总票房突破12亿,创华语电影历史新高
更惊人的是口碑。猫眼评分9。6,淘票票9。5,豆瓣开分直接飙到8。9,评论区清一色写着:“这才是我们的真实生活。”
就连一向苛刻的知乎,热榜第一的问题也是:“为什么《人在?途》让我哭得像个孩子?”
有一位网友的回答被顶到最高:
>“因为我爸就是老李。他今年六十二岁,干了三十年瓦工,背驼得像虾米。去年年底摔了一跤,腰椎间盘突出,医生说不能再干重活了。但他还是买了张站票回家,说‘不回去,年就不是年了’。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直在找他的影子。后来我发现,不止是我爸,我身边每一个沉默的人,都在里面。原来我们从来不是隐形的。原来有人一直在看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