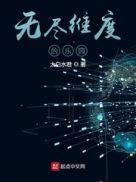笔趣阁>华娱:屁股坐正了吗?你就当导演 > 第187章 韩三品之谈定角之问815(第3页)
第187章 韩三品之谈定角之问815(第3页)
>你对我说世界多美,
>我说,你的声音就是最美的风景。
>
>我看不见国旗飘扬,
>但我听得见国歌嘹亮;
>那是我心中永不坠落的太阳。”
最后一个音落下,全场起立鼓掌。有人流泪,有人跪地合十。评委们久久无法评分,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这不是比赛,是洗礼。
演出结束后,一位退休音乐教授找到曹忠,颤抖着说:“我教了一辈子声乐,今天才知道,什么叫纯粹的声音。”
影片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难度前所未有。如何让观众“听见”视觉之外的世界?剪辑团队尝试多种方案:增强环境音、加入触觉描述旁白、采用3D环绕声技术模拟空间感。最终,他们在景田建议下做出大胆决定??全片三分之一时间采用“黑屏聆听模式”,即画面全黑,仅保留声音,引导观众闭眼体验盲童的世界。
试映会上,一位观众反馈:“我从未如此认真地听过一首歌。当世界变黑,我才真正‘看见’了光。”
2026年春节前夕,《听见光》在北京举办全球首映礼。入场前,每位观众都被蒙上双眼,由志愿者牵引至座位。放映过程中,影院灯光全程关闭,唯有银幕偶尔闪现极简动画或盲文投影。
片尾,卓玛的声音缓缓响起:
>“以前我以为光明是颜色,后来我知道,它是温度,是拥抱,是有人愿意蹲下来,对着我的耳朵说:‘我在。’
>
>如果有一天你也陷入黑暗,请不要害怕。
>因为总会有一首歌,穿越风雪,奔向你。
>那就是光,在人间行走的声音。”
全场静默数秒,随后掌声如潮水般涌起。许多人摘下眼罩,满脸泪水。
次日,《听见光》豆瓣开分9。8,猫眼满分率95%。央视新闻专题报道:“这不是一部关于残疾的电影,而是一部关于人性光辉的史诗。”教育部再次发文,建议将影片纳入生命教育课程。多地特殊学校发起“听见光计划”,组织视障学生创作音频日记。
而最让曹忠动容的,是一封来自青海玉树的信。写信人是一位失明多年的老人,他在孙子帮助下听完影片录音版,写道:
>“六十岁那年我失去了眼睛,从此不愿出门,觉得活着成了负担。可昨晚我听了你们的片子,哭了好久。原来看不见不可怕,可怕的是心也瞎了。今天早上,我让我孙女扶我去菜市场,我说我要买一把葱,亲手做顿饭。她说爷爷你笑了,多久没见你笑了。”
>
>“谢谢你们让我明白,耳朵也能看见春天。”
曹忠把信读了三遍,然后轻轻贴在办公室墙上,挨着前两封信。窗外,初春的阳光斜照进来,落在那盆枯萎已久的绿萝上??不知何时,竟冒出了一簇嫩芽。
他拨通赵海城电话:“下一个项目,我想拍边境线上的国界碑守护员。”
“又是苦地方。”赵海城叹气。
“嗯。他们一年见不到几个人,却天天擦拭着代表国家尊严的石头。有人说他们是孤独的,可我觉得,他们才是最不孤单的??因为背后站着十四亿人。”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传来一声笑:“行,我还是那句话:怕黑,所以点灯。只要你还敢点,我就敢跟着你闯。”
挂了电话,曹忠翻开新剧本。风掀动纸页,扉页上三个大字墨迹未干:
**《守界人》**
桌角,那盆绿萝的新叶微微抖动,仿佛回应着某种无声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