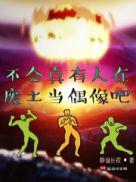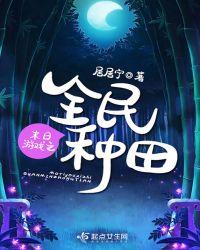笔趣阁>状元郎 > 第三一四章 西南得朋(第2页)
第三一四章 西南得朋(第2页)
最终,圣旨再降:刑部御史团撤回,秦某通缉追拿;浙江新政继续推行,增设监察御史一名,由皇帝亲选,监督执行。
风波暂息,然苏录心中并无轻松。
他知道,敌人不会善罢甘休。这一次,他们败在低估了民心的力量。
冬去春来,女子学堂已运行半年,学生人数增至五百,课程除《千字文》《女诫》外,还增设算术、地理、医理浅说。许多贫家女学会记账、识图,甚至能为乡里调解纠纷。一日,一名十岁女童在课堂提问:“先生,为何男子可考秀才,我们却只能旁听?既然都能读书,为何不能同试?”
满室寂静。
苏录望着她明亮的眼睛,久久不能语。他想起自己初见周延儒时也曾这般发问,而今轮到他回答下一代。
当晚,他伏案疾书,起草《请开女子科举疏》,条陈八利:一可广储人才,二可教化民俗,三可助贫户脱贫,四可促男女平等,五可树国家新风,六可破世家垄断,七可激全民向学,八可彰圣朝仁治。写毕,泪湿纸背。
次日,他携疏求见周延儒。
巡抚大人读罢,沉默良久,终叹道:“你说得都对……可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们将挑战千年礼法。”苏录平静道,“但也意味着,第一个女状元,可能就坐在那间教室里。”
周延儒苦笑:“你以为我不愿?可眼下局势刚稳,若再掀巨浪,恐怕连现有成果都会保不住。”
“所以不必全国推行。”苏录恳切道,“请大人允我在杭州试点??设‘女子特科’,三年为期,独立考评,不入正榜,仅授‘女学士’称号。既不失礼制体面,又能探路前行。”
周延儒盯着他,忽然笑了:“你啊……总能找到那条最难走却又最该走的路。”
半月后,在周延儒力保下,“女子特科”获准试行。消息传开,全省轰动。报名者逾两千人,年龄自十二至四十不等,有闺秀、寡妇、婢女、渔娘,甚至一位六旬老妪,拄拐而来,颤声道:“我年轻时偷听私塾三年,如今终于能光明正大考试了。”
考试当日,苏录亲自主考。他站在贡院门口,看着一个个女子身着蓝裙步入考场,有的紧张搓手,有的昂首挺胸,还有一位盲女由妹妹牵引入场,手中紧握盲文凸点板??那是她自学摸索制成的“触读器”。
那一刻,他仿佛看见未来的光。
然而,就在放榜前夕,意外突生。
一名考生被人举报“冒名顶替”,经查竟是绍兴富商之女假冒佃户女儿身份报考,企图骗取“女学士”头衔以抬高身价。此事一经披露,舆论骤变。保守派官员群起攻讦,称“妇人干政已违祖训,何况弄虚作假?足见女子不宜参与功名!”更有京中御史上奏,要求立即废除此制,严惩主事者。
苏录几乎窒息。
他知道,这绝非偶然舞弊,而是精准打击??敌人为摧毁女子教育,不惜制造丑闻。
更令他心寒的是,举报人竟是那位曾感动杨慎的绍兴女孩之父。原来其家受人贿赂,被迫出面作伪证,事后才悔恨痛哭。
苏录亲自登门安抚,老人跪地叩首:“苏大人,我错了……可我儿子被抓走了,他们说若不举报,就要治他‘私通匪类’之罪!”
苏录扶起老人,声音沙哑:“责任不在你。错的是这个逼良为盗的世界。”
他连夜写下《辨诬启事》,公布全部考生资格审查流程,强调绝大多数皆经乡里公示无异议,并附上百名真实寒门女学子的家书与履历。同时,他请求司法介入调查“冒名案”背后黑手。
七日后,真相浮出:幕后策划者竟是省内某盐运使副手,其妻妹原为妾室,因妒忌新政让婢女也能读书,竟出资买通商人设局陷害。
案情揭晓,公众情绪反转。百姓纷纷指责“权贵怕女人聪明”,民间流传起一首童谣:“男儿读书做大官,女儿读书管厨房?不如一把火烧掉旧礼单!”
最终,首批三十名“女学士”如期授衔。典礼上,那位六旬老妪拄拐登台,接过证书时老泪纵横:“我爹说女子识字会克夫……可你看,我活到六十,丈夫早死了,我还是活得比谁都明白。”
台下掌声如雷。
苏录站在人群中,默默注视这一切。他知道,这场战争仍远未结束,每一寸进步都要付出代价。但他也看到,火种已然点燃,纵有狂风暴雨,也无法将其彻底熄灭。
那一夜,他又收到一封信。
没有署名,只有一页白纸,中央画着一盏油灯,灯芯燃尽,却仍有微光挣扎闪烁。
他凝视良久,提笔在旁边写下两行小字:
“灯虽将尽,光未消亡。
只要有人愿添一滴油,它就能再亮一瞬。”
然后,他吹灭烛火,推开窗户。
东方既白,晨曦初露,远处学堂已有琅琅书声随风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