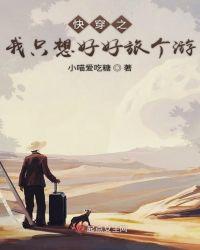笔趣阁>凤谋金台 > 160167(第3页)
160167(第3页)
李文韬心中大喜,面上却沉稳如水。他躬身一礼,道:“陛下英明。国之根基,系于储位。拖延日久,朝野震荡。”
李慧瑾神色依旧没有波动,但她眉宇间那一点沉凝,像是藏着千钧压力。她端坐不语,只是看着李鸾徽。
李鸾徽却继续说下去:“经过这些日子的考察,朕觉着,晋王李起年,年纪适中,脾性温和,又无兄长结党之势,朕看他甚合。”
这话一出,李文韬心中已有把握。他知道,这是李鸾徽、长公主,乃至整座权力机器,在清洗冯知节、放任西平、封锁李起云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表态——要将李起年扶上太子之位。
这一局,他们下定了决心。
李文韬抬眼,眼底一闪而过的光芒藏不住得意。他缓缓转头看向李慧瑾,她的神色没有任何回应。
他意识到,她始终是个冷静的人,她不会高兴,也不会悲伤,难以揣测,不同场合戴着不同的面具。李慧瑾是个明白的人,明白权力之路就是一场牺牲与成全的博弈。
“此事是否由臣起草诏书?”李文韬问。
李鸾徽点头:“草诏,由你与礼部一同拟定,明日呈上。”
这一刻,李文韬有了一种一览众山小,站在峰顶的感觉。三代帝王,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越发得少了。
所有的布棋、算计、投诚、退让,都在这一刻获得了回报。
他已然是拥太子之相。
这一边,泰王府内。
李起云刚刚被“准许”离开那座幽闭偏殿。
数日未见天光,他整个人消瘦不少,眼底的血丝像枯枝丛生,整个人带着压抑的疲倦。可他一回府,连茶水刚送到手上,还未喝了一口,前厅的侍从就跌跌撞撞跑来报信。
“殿下、殿下!……圣旨已下,太子已定——”
李起云回头,看到了张向天也站在门外,神色肃然。
“谁?”他嗓音沙哑,却急促。
“……晋王李起年,封为太子。”
那一瞬间,他手中茶盏“啪”地落地,碎成几瓣,滚落的茶水在台阶上浸湿一片,像是血一样地蔓延。
他输了。
他……输了?
与此同时——
徐圭言正在书房中,听着一名机要亲信快步而入,带来消息。
“太子已定。”那人说,“长公主、李相皆出席朝议,陛下亲口宣旨,封李起年为太子,明日颁告百官。”
她没有立刻回应,指尖在书案上一点一点轻敲,像是在思索、也像在计数。
许久,徐圭言叹出一口气,转头望向窗外,远处楼阁间隐隐传来宫钟之音。
她忽而想起冯知节,想起他跪在殿前的身影,想起他离开长安时,沉默不语、目光冷冽的样子。
冯知节被清出局,这只是个开始。
皇储确立——朝局重构。
徐圭言没有赢的感觉,她低头看着手中的书卷,一字都看不进去。
而就在旨意传下的当夜,东市里有个老艺人喝得大醉,在酒楼角落自言自语:“冯将军走了,太子定了……可你们都不知道,真正的乱,还在后头。”
话音未落,他突然闭口不言,跌入昏睡。
不知何时,长安城内流言四起,“太子者,非真龙也。”
圣旨已下,金銮殿上,玉玺封蜡尚未冷透。
东宫尘封许久的宫门重新开启,李起年身披暗金织凤的太子朝服,在徐圭言与礼部尚书陆明川的引领下,跨过那一段玉阶时,他的脚步无比稳重。
他低头看着那层薄雪与残霜交错的地面,仿佛看到前人的血影在石缝中未干。
徐圭言被安排到东宫一旁的小院中办公。
那是先帝早年为太子亲信设置的文书院,光线幽暗,却背靠御花园,是座静谧的所在。
她推开厚重的木门,案几上放着新送来的政务卷宗,未揭封的信札堆成一叠。窗纸被风吹得颤动,一缕阳光照在她沉默的面容上——她知道,从此再无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