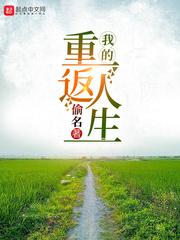笔趣阁>草芥称王小说TXT最新章节列表 > 第125章 规划为温州皮卡丘CT盟主加更(第5页)
第125章 规划为温州皮卡丘CT盟主加更(第5页)
??最终,智者决定建立“言冢”
,自愿遗忘部分历史,换取和平;
??而最后一任守陵人留下预言:“待草芥称王之日,铃声自会重鸣。”
阿启跪倒在地,泪流满面。
他终于明白,《草芥录》为何开篇即言:“王者非坐金殿者,乃肯为无声者发声之人。”
下山途中,他写下一封信,命沙鸢送往长安:
>“陛下不必恐惧记忆。
>它不是洪水,而是种子。
>有人选择埋葬它,我们选择种下它。
>若这天下终将因真相而动荡,请记得??
>是你们先杀了安宁。”
七日后,诏书再颁:全面开放皇室档案馆,允许民间抄录历代禁书;赦免所有现存“记名者”
;设立“鸣钟日”
,每年祭奠因言获罪者。
裴景和寄来的那页残稿被刻成石碑,立于国子监门前。
冬至那天,第一场雪落下。
长安街头,一群盲童手拉手走过朱雀大街,齐声朗诵《草芥录》。
路人驻足聆听,有人掩面而泣,有人默默跟诵。
铜壶滴漏、檐角风铃、甚至锅碗碰撞之声,都在特定时刻拼出同一句话:
“我记得。”
与此同时,在北境流民营旧址,一场简单的葬礼正在进行。
棺木中躺着一具无名骸骨,据考证正是阿福遗骸。
他在启动青铜铃后彻底消失,只留下扫帚柄中的遗书:
>“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
>但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
>如果记住是一种罪,
>那我甘愿永堕地狱。”
坟前无人说话,唯有三百纸铃随风轻摇,汇成一片寂静的潮声。
春雷响起时,祁连山的裂缝又拓宽了一尺。
幽蓝晶光中,隐约可见无数细小符号缓缓上升,如同沉眠千年的文字正逐一苏醒。
阿启站在高处,怀中抱着一个新生婴儿??那是陈九娘收养的孤儿,脐带缠绕着一枚微型陶埙。
“给他取个名字吧。”
陈九娘问。
阿启望着远方初升的太阳,轻声道:“叫‘闻’吧。
听见的闻,
也是闻名的闻。”
风起,铃响,万里山河俱在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