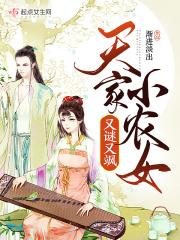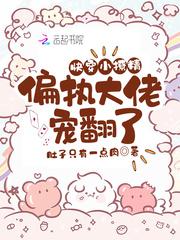笔趣阁>草芥称王小说TXT最新章节列表 > 第132章 江南消息(第1页)
第132章 江南消息(第1页)
潘小晚坐在梳妆镜前,由侍女巧舌小心服侍着装扮。
先是将一对雪白的卧兔儿暖套套在手上,兔毛蓬松柔软,衬得她指尖愈发纤细。
接着围上一圈油光水滑的貂鼠风领,暖融融的毛领裹住半张俏脸,只露出一双。。。
春阳初升,融雪顺着屋檐滴落,在青石板上敲出清脆的节拍。
阿启坐在记忆传承馆后院的老槐树下,手中握着一卷尚未装订的《众声录》手稿。
纸页泛黄,墨迹未干,字里行行皆是各地传来的讯息:某村重修族谱,补入百年前被除名的女子;某中学师生徒步百里,只为在荒坡上为一位无名流放者立碑;西北边陲小镇,一群老人自发组织“口述史夜会”
,每晚轮流讲述自己亲历的沉默岁月。
他一页页翻看,指尖微颤。
这些不再是孤影独行的火种,而是千万人共同点燃的星野。
风拂过树梢,叶片轻摇,仿佛回应着纸上的名字与故事。
忽然,一阵脚步由远及近,轻却急促,像是怕惊扰了这份宁静。
来的是周念,那个曾在雪岭土地庙前递上布条的少年。
三年不见,他已长成青年,肩背挺直,眼神沉静如深潭。
他手中提着一只木箱,外裹油布,边角磨损严重,显然跋涉已久。
“先生。”
他在阿启面前站定,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我来了。”
阿启抬头,目光落在他脸上,又缓缓移到那木箱上。
“你走得很远吧?”
他问。
“从岭南到西漠,再折返北方。”
周念将箱子放下,解开绳索,“这是我奶奶留下的暗账全本,还有这些年我收集的证词、信件、遗物清单……一共三百七十二份,都是‘静土计划’中被抹去的人。
他们没有墓,没有碑,甚至连档案里的名字都被涂黑。
但现在,有人开始记得他们了。”
阿启伸手抚过箱盖,指尖触到一道刻痕??一个小小的“林”
字,歪斜却坚定。
“林照的事,后来呢?”
他低声问。
周念眼底闪过一丝光:“去年冬天,我们在西漠戈壁找到了一处废弃劳改营遗址。
营地早已塌陷,但地下仓库还存着一些登记册残页。
其中一页上有他的编号和最后记录:‘精神顽固,转入隔离区,生死不明。
’我们顺着线索挖了七天,终于在一棵枯死的胡杨旁发现了半块日记本碎片。
上面写着:‘今日教孩子们背《正气歌》,他们小声跟着念,像春天的第一阵风。
若我不能归,愿此声不绝。
’”
他说完,从箱中取出那片泛黑的纸页,轻轻放在阿启膝上。
阿启久久凝视,喉头滚动,终未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