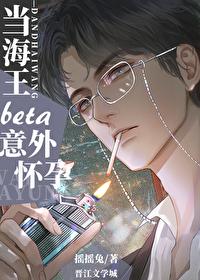笔趣阁>草芥称王小说TXT最新章节列表 > 第133章 杨灿是墨者(第2页)
第133章 杨灿是墨者(第2页)
>他还想看一眼故乡的春天。”
录音戛然而止。
阿启起身走到窗前,望着漆黑山谷。
雨滴敲打屋檐,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叩问历史之门。
他忽然想起少年周念说过的话:“我们不是要推倒高墙,是要让墙后的声音传出来。”
如今,这些声音正穿越海峡、翻越高山,汇入这一册《众声录》的洪流。
翌日清晨,阿启亲自执笔,在新一页写下:
>**陈文彬,四十五岁,编辑,因坚持报道灾情实况遭拘押致死。
遗愿:再见故土春樱。
**
随后,他取出一枚铜钉,将这张纸牢牢钉在驿站主厅的“归名墙”
上。
沈兰带着几位志愿者开始复印副本,准备送往各地分会。
与此同时,一位年轻女孩自海外来电,自称是李志远的外甥女,已在澳洲生活三十年。
她说:“外婆昨晚梦见舅舅回来了,穿着旧军装,站在村口喊娘。
我查了移民档案,发现七十年代末有个同名同姓的人偷渡至越南,后来失联……也许他还活着。”
阿启握着电话,久久无言。
最终只道:“请你把所有线索寄来。
只要有一线可能,我们就不会停止寻找。”
数日后,阿启再度启程北返。
途中经一座废弃火车站,站名牌已倾颓,铁轨掩于荒草。
一名老铁路工人蹲在月台边抽烟,见他驻足,便主动搭话:“这儿曾是‘静土计划’的转运点。
半夜常有闷罐车驶过,没人知道车上是谁,只知道下车的人,再也没回来。”
阿启蹲下身,与他对视:“您还记得车牌号吗?”
老人摇头:“记不得了。
但我记得声音??孩子们哭得很小声,像是被人捂住了嘴。
有个小女孩一直在背诗,背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她背了整整一夜。”
阿启心头剧震。
林照教过的诗,竟以这种方式,在黑暗的车厢里延续。
他在笔记本上记下这段口述,并标注地点坐标。
离开前,他在月台立了一块木牌,上书:“**此处曾有过哭泣,也曾有过诗句。
请勿遗忘。
**”
回到记忆传承馆那日,正值秋分。
庭院中桂花飘香,碑墙前人群络绎不绝。
一位盲眼老太太由孙女搀扶而来,手持一根竹杖,杖头刻着“寻夫”
二字。
她摸索着碑面,口中喃喃念着丈夫的名字:“赵承业……你听得到吗?我带你最爱吃的梅干菜来了……”
工作人员上前引导,很快在东南区找到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