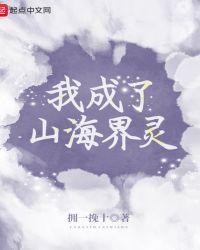笔趣阁>草芥称王小说TXT最新章节列表 > 第139章 缠枝孕事(第3页)
第139章 缠枝孕事(第3页)
他看着我,笑着说:‘你现在安全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教错的东西了。
’”
台下有人抽泣。
“三年前,我在旧书市场淘到一本残破的《呐喊》。
翻开第一页,上面竟有我丈夫的批注。
那一刻我才明白,他没有忘记,他只是不能再表达。
于是我把这本书复印了三千份,偷偷放进全市各个图书馆的书架缝隙里。
我希望有一天,有个孩子会问:这个批注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写这些?”
掌声如雷。
就在此时,场馆外围警报突响。
安保人员截获一名伪装成清洁工的男子,搜出身上的微型干扰装置,型号与此前袭击传承馆的设备一致。
更令人震惊的是,此人手机中存有一份名单??列出了全国五十三位核心证人及其家属住址,标注等级A至C,A类为“优先清除”
。
警方介入调查,顺藤摸瓜挖出一个隐藏多年的地下组织“净忆同盟”
。
该组织成员多为当年“清源计划”
执行者的后代,坚信父辈所做一切乃为国家稳定必要之牺牲。
他们在社交媒体悄然培育“遗忘派”
青年社群,灌输“历史包袱论”
“情绪消费主义批判”
等话语,试图将记忆抗争污名化为“精神内耗表演”
。
舆论再度沸腾。
某知名学者在访谈中直言:“有些人沉迷于痛苦叙事,把民族记忆变成一场永不落幕的葬礼。
难道我们要永远活在仇恨中吗?”
话音未落,微博热搜即被攻陷。
数百万网友贴出自家老人沉默的背影照片,配文:
>“他们不是不想忘,是不敢想。”
>“你说放下,可我们连坟都没有。”
>“如果连痛都要禁止,那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与此同时,《众声录》上线新功能“回声地图”
:用户可在电子地图上标记家族记忆坐标,点击任意地点即可收听当地上传的真实录音。
短短一周,地图点亮超过十万点,从东北林场到南海渔村,从边疆哨所到都市老巷,无数微弱却坚定的声音交织成网。
清明前夕,北京某中学发生震动全国的事件:一名高二学生在思政课上公开质疑教材中关于“社会稳定过渡期”
的表述,要求老师出示原始档案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