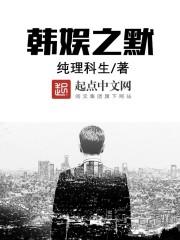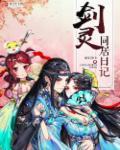笔趣阁>仙工开物宁拙孙灵瞳笔趣阁小说大结局完整版 > 第420章 王命仙资 万偃魔怪(第4页)
第420章 王命仙资 万偃魔怪(第4页)
年轻人深吸一口气,重新开始。
渐渐地,动作变得流畅起来。
锅中的粥翻滚着,香气愈发醇厚,竟引得附近野猫聚集在墙头,不再嘶叫,只是安静蹲坐,鼻子微微翕动。
傍晚,第一顿集体晚餐准备完毕。
一百多人围坐在院中,自带碗筷,按顺序领取。
没有喧哗,没有插队,只有勺子碰碗的轻响和偶尔的低语。
有人吃完后默默清洗碗具放回原处;有人主动帮行动不便的老人打饭;几个孩子自发组成清洁小组,擦拭桌面、扫地倒水。
宁小满端着碗坐在角落,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眼眶发热。
他曾以为改变世界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现在才懂,最深刻的变革,往往始于一顿安静的晚饭。
夜幕降临,新一批异象传来。
印度贫民窟的一位盲女,在母亲去世后第一次独自生火做饭。
当她摸索着往锅里加水时,火焰自行燃起,照亮了她苍白的脸。
她笑着说:“妈妈,我学会啦。”
澳大利亚内陆牧场,一名牧羊人收工归来,发现自家老旧灶台泛起乳光。
他不信邪,试着煮了壶茶,结果茶水入口瞬间,脑海中浮现出二十年前亡妻泡茶的模样。
他抱着茶壶嚎啕大哭。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北极冰盖之下,一座沉没百年的蒸汽时代科考站遗址中,一台机械锅炉突然重启。
内部铭牌显示,建造者署名为:“宁拙,1923年”
。
“他去过那里?”
宁小满震惊。
老学者点头:“你父亲失踪的三年,并非消失。
他在全球奔走,埋下火种。
南极、深海、荒漠、极地……每一处人类挣扎求生之地,都有他留下的灶基。
如今,它们都被唤醒了。”
宁小满久久无言。
他终于明白,父亲从未离开。
他的身影藏在每一次有人为陌生人点亮炉火的瞬间,藏在每一口热饭暖胃的满足里,藏在那些不愿让任何人饿着的执念中。
第三日清晨,全球灶台数量突破千关。
南街七号的铁锅悬浮至屋顶高度,火焰冲天而起,化作一道乳白色光柱,直贯云霄。
星图完全成型,三百六十度环绕庭院,标记着每一处燃烧的灶台,宛如银河倾泻人间。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厨房在同一秒发生异变。
纽约公寓里,白领女子正用微波炉加热速食餐,忽然设备融化重组,变成一只陶锅,粥香四溢;撒哈拉难民营中,妇女用沙土堆砌简易灶台,刚点燃柴草,火焰便转为乳白,锅中小米自动翻滚;甚至在空间站里,失重环境下的食物包漂浮不定,却突然聚拢成球,表面浮现符文,缓缓蒸腾出热气。
所有人心中同时响起一段旋律??正是《炊者吟》的完整版本。
>“五更天,粥已成,
>六亲不认亦同羹。
>七窍通,烟火明,
>八方风雨共此灯。
>九死犹燃心一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