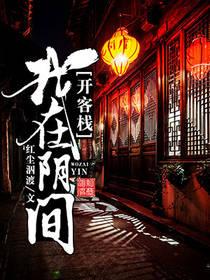笔趣阁>仙工开物宁拙孙灵瞳小说TXT全集免费下载 > 第418章 散布流言不这是正义的揭发(第1页)
第418章 散布流言不这是正义的揭发(第1页)
陈三连忙告罪。
宁拙手指点了点桌面,目光冷冽:“你初来乍到,还不熟悉我的为人。
念你第一次犯错,这就算了,下次不可再犯。”
陈三改变跪姿,双膝触地,连忙保证。
宁拙唔了一声,背靠椅背,。。。
晨光如纱,轻轻覆在南街七号院的瓦砾之上。
炊烟未散,缭绕于残垣断壁之间,像一条不肯离去的魂。
老学者坐在门槛上,碗已空,筷已净,手却仍停在膝头,仿佛还托着那顿饭的重量。
他不看天,也不看地,只盯着石台上那只陶碗??它静静立着,釉面映出微光,像是吸进了昨夜所有的火与声。
学生们陆续醒来。
他们在院中席地而卧,裹着外套,脸上沾着草屑和露水。
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急于收拾行装。
他们昨夜所见,不是幻觉,不是梦,而是某种比现实更沉重的真实压进了骨髓。
有人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仿佛还能感受到锅影投下的温度;有人望着铁锅,那口如今安静如墓碑的大锅,底上那个“圆中一点”
的印记已深深烙入金属纹理,如同星辰初生时留下的胎记。
“老师。”
终于有个学生开口,声音干涩,“我们……真的要建灶房?”
老学者缓缓点头,起身,走向铁锅。
他伸手抚过那圈印记,指尖微微发烫。
“不是我们要建。”
他说,“是它选了这里。”
话音落处,地下又是一阵轻颤。
不是乳白流质渗出,而是一缕细若游丝的热气自锅底裂缝升腾而起,在空中盘旋片刻,竟凝成三个字:
>“等一人。”
众人屏息。
“谁?”
有人问。
老学者闭眼,似在倾听风里的低语。
“不知道。”
他睁开眼,“但宁拙的母亲说过,‘她回来了’。
现在又说‘等一人’……也许,是另一个节点要归位。”
就在这时,巷口传来脚步声。
不急不缓,踏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回响。
众人回头,只见一个女子走来。
她约莫四十岁上下,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肩背竹篓,发髻松散,脚上一双旧布鞋沾满泥尘。
她面容普通,眼角有细纹,右手食指有一道陈年烫伤的疤痕。
可当她走近院门,铁锅突然嗡鸣一声,锅底印记泛起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