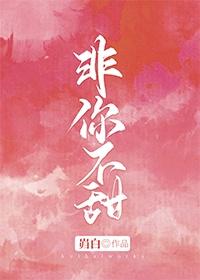笔趣阁>大明兽医,开局给朱标续命 > 163 天降横祸(第2页)
163 天降横祸(第2页)
“人心难测,利字当头。”董桂花低声道,“然正因如此,才更需雷霆手段。臣恳请殿下,即刻成立‘煤案专查司’,由锦衣卫、大理寺、御史台三方共理,不受六部节制,直隶东宫。唯有跳出旧衙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方能彻查到底。”
朱标沉吟片刻,终是点头:“准奏。卿为总提调,全权处置。”
“臣领命。”
当夜,董桂花亲赴贾文亮宅邸验尸。
屋内阴冷潮湿,绳索仍悬于梁上,尸体早已入棺。他命人开棺重验,细细查看颈部勒痕、指甲血渍、舌骨状态,又取其衣袖褶皱处微量粉尘化验。
半个时辰后,他立于庭院之中,对随行医官道:“此人非自缢。”
“大人?”
“自缢者,绳索多呈八字不交,勒痕由耳后斜向下颌,且深度均匀。此人颈侧有明显抵抗伤,左手掌缘有擦伤,显系挣扎所致。再者,其舌尖微露,舌骨完好,不符合典型缢死特征。”董桂花冷冷道,“更何况,这般要紧人物,家中竟无护卫值守?门窗虽闭,但后窗窗棂有细微刮痕,应是凶手从外潜入,杀人后布置假象。”
医官骇然:“那……是谁下的手?”
“不知道。”董桂花合上眼,“但我知道,他们怕他说出什么。”
翌日清晨,金陵城内外张贴告示:
**“奉太子令旨,凡参与蜂窝煤试点事务者,若有知情不报、通风报信、贪墨舞弊之行为,一经查实,不论官职,一律革职下狱,家产抄没!”**
同时,三艘货船已分别驶入扬州、杭州、福州港。
扬州码头,一名身穿绸衫的中年商人亲自登船验收,正是当地巨贾周元泰。他捻须微笑,挥手示意手下搬运:“好煤啊!听说这是太子殿下的‘惠民神物’,将来必成南北奇货!”
然而就在卸货至一半时,一名工人突然惊呼:“东家!这块煤怎么这么重?裂开了!”
众人围上,只见蜂窝煤断面中赫然嵌着一枚铜片,上刻“京工甲三?0427”字样。
周元泰脸色骤变,立刻喝令:“停下!全部封箱,原船返航!”
可惜晚了。
岸边茶楼二楼,一名戴斗笠男子悄然离去,脚下马蹄声疾驰而去,直奔城外军营。
同一时刻,北平燕王府,朱棣正于书房阅卷。
烛火映照着他半边脸庞,威严中透着阴鸷。亲兵入报:“启禀王爷,南方密信到。”
他接过信笺,展开一看,嘴角微扬:“煤已易,慎行……呵呵,董桂花,你果然聪明。”
身旁谋士道:“殿下,既然计划受阻,是否暂缓南图?”
“暂缓?”朱棣冷笑,“正因受阻,才更要动。他们以为换掉几块煤就能断我血脉?殊不知,我要的从来不是煤,而是人心。”
他提笔蘸墨,在纸上写下八个字:**“薪尽火传,势不可挡。”**
而后唤来心腹:“传令下去,放出风声??江南百姓试用太子新炉,一夜之间中毒十余户,三人身亡。罪魁祸首,便是那‘蜂窝煤’!”
谣言如野火燎原,三日内席卷江淮。
扬州街头已有泼墨大字:“毒煤害民,太子失德!”
杭州书院学子集会,质问官府:“既言便民,为何致人死亡?”
更有江湖术士装神弄鬼,称“黑石吸魂,青烟夺命”,煽动百姓焚毁炉具。
消息传至南京,朝堂震动。
朱标怒极拍案:“荒谬!蜂窝煤经数十次测试,绝无毒性!谁在造谣?!”
黄子澄忧心忡忡:“殿下,纵使真相清明,奈何流言滔天。百姓只信亲眼所见,不信官府辩解。若不能迅速澄清,新政未兴,先失民心。”
朱标目光转向董桂花:“你有何策?”
董桂花神色平静:“臣请殿下允许一事。”
“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