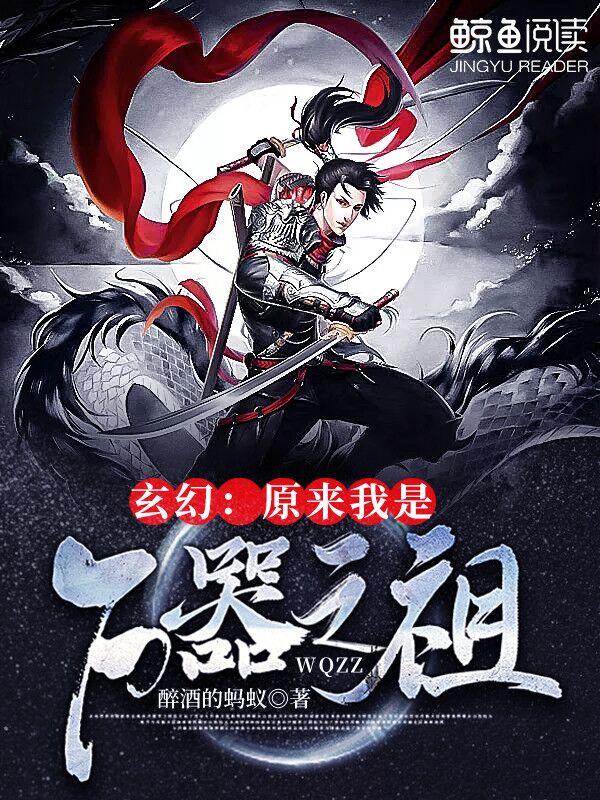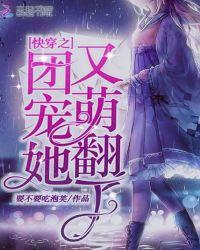笔趣阁>马寻忽悠华娱三十年(最新更新章节免费阅读 > 第七百四十章 超越阿凡达大甜甜的魄力(第1页)
第七百四十章 超越阿凡达大甜甜的魄力(第1页)
2010年的贺岁档还没有真正的开始,但一条新闻就先刷爆了网络!
“《让子弹飞》官宣突破9亿票房!”
“国产第一部破9亿的电影!
那么,有没有可能破10亿?”
“《让子弹飞》有可能突破十。。。
秋意渐深,滨海县的清晨总带着一层薄雾,像是天地间尚未醒透的梦。
苏晚照例六点起身,推开窗,让凉风灌进屋子。
她已年过六十,两鬓斑白,可眼神依旧清亮,像能穿透岁月的尘埃。
床头那支缠红绳的钢笔静静躺在玻璃瓶旁,墨水早已干涸,却从未被替换??她说,这支笔写过的信,都飞去了比天空更远的地方。
她穿上旧毛衣,提着竹篮走向后院。
花海比往年更加繁茂,琉璃花的蓝光在晨雾中浮动,如星子坠地。
十年前种下的那一株如今成了母株,根系蔓延至整片土地,每逢雨夜便释放出微弱频率的波动,科学家称之为“情感谐振场”
。
据监测,这种波动能显著降低周边居民的焦虑指数,甚至影响梦境内容。
苏晚蹲下身,指尖轻抚一片花瓣。
刹那间,一段陌生记忆涌入脑海:一个少年坐在书桌前,窗外是柏林的雪夜,他正用颤抖的手写下第一封信??收件人是他五年前车祸去世的哥哥。
信纸烧尽时,火焰呈现出奇异的螺旋状,灰烬未散,竟在空中停留三秒,拼出两个德文字母:“Danke”
(谢谢)。
她怔住。
这不是她的记忆,也不是她教过的学生。
可那股熟悉的温度,那种倾诉后的释然,分明与归零站废墟里曾流淌的情绪同源。
“又来了。”
她低声说。
近年来,她时常接收到来自远方的情感残影。
起初只是零碎画面,后来逐渐清晰,仿佛全球范围内的“心灵书写”
行为正在编织一张无形之网,而她是其中一个节点。
有人称她为“信使导师”
,也有人暗地里叫她“最后的守井人”
。
但她从不回应这些称呼,只坚持做一件事:每月十五,准时打开枯井机关,送走一批信。
今天正是十五。
上午九点,教室里坐满了学生。
这门“写作与遗忘”
课早已不限于本校,每年都有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前来旁听。
他们中有作家、心理医生、程序员,甚至还有几位退休外交官。
课程没有教材,不考试,唯一的作业就是写信??可以给活着的人,也可以给死去的、未来的、虚构的,甚至是宇宙本身。
苏晚站在讲台前,声音温和却不容置疑:“记住,信的本质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完成一次自我对话。
当你愿意面对那个不敢见光的自己,奇迹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