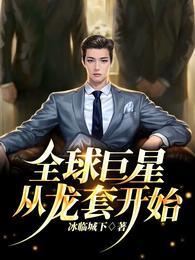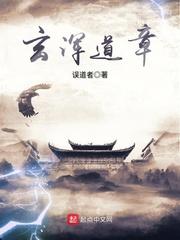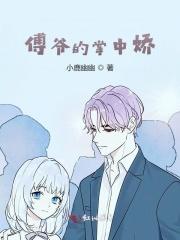笔趣阁>红楼:我,贾环,抄书百倍奖励!贾环全文完整版 > 第443章 定风波(第1页)
第443章 定风波(第1页)
皇后、太子、张岳、戴权、四人坐在凤藻宫内。
在一旁,是皮肤已经发白的皇帝。
巨大的肉体盖着棉被,胸膛没有任何起伏。
张岳的眼神很是沉重,太上皇死的那个夜晚还在他的脑海。
他规劝。。。
徐寿的锦城工坊成了风暴眼。
工匠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肩挑背扛着图纸、木模、铁器、药方,甚至还有用油纸层层包裹的秘制药粉。
他们或衣衫褴褛,或身披粗麻,却无一不是眼神灼亮,步履坚定。
有人跪在专利司门前,捧着祖传三代的织机图样,声泪俱下地请求登记;也有人连夜赶路三百里,只为抢在第一批名单中留下姓名。
更有甚者,竟将自家祖坟里的“机关椁”
拆了半边,取出藏于棺底的青铜齿轮组,声称是“先祖所遗飞天之器”
的核心部件??虽然后经查验不过是民间丧仪用的自动启闭香炉机关,但那份热忱,却让工部老吏都为之动容。
而真正掀起滔天巨浪的,是徐寿呈上的第一份《乾纶纺丝法》专利文书。
那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徐寿便带着三名弟子,抬着一口红漆木箱步入专利司大堂。
箱中并非金银,而是整整三十卷羊皮图谱、五套精密铜模,以及一束以特制琉璃管封装的原始乾纶丝线。
他当众焚香叩首,按下手印,一字一句朗声道:“臣徐寿,愿以毕生所研‘乾纶九转纺丝术’,献于朝廷,受专利之制,享匠人之荣。”
话音落下,满堂寂静,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
这份专利,被定为甲字一号。
工部依例勘验七日,由牛顿亲自主持,召集十二位格物院学士、六名尚工局老匠、两名西洋技师共同审定。
最终结论:此法融合水力传动、温度恒控、多轴牵引三大创新,较之旧式缫丝,效率提升十七倍,成品坚韧度逾蚕丝三倍有余,确属划时代之创举。
分润定为:朝廷七分,徐寿及其工坊三分。
然因乾纶乃战略物资,皇帝特旨加恩,准其十年内保留四成收益,并赐“格物昭勋”
金匾一面,许其子入国子监旁听格物课程。
消息传出,天下震动。
原本对专利制持观望态度的节度使们,终于坐不住了。
西蜀节度使李崇义当即上表,称境内有“火油井自燃之奇技”
,愿献出提取与储运之法,换取专利授权;北疆安西都护府更派人快马加鞭送来一封密奏,言当地胡匠已试制出“风力鼓风机”
,可使冶铁炉温突破古法极限,若得朝廷支持,一年内可建十座新式铁坊。
就连一向闭关自守的江南徐家,也在压力之下悄然派出使者,携《海船龙骨榫接二十式》前来登记。
昔日视若性命的造船秘技,如今不得不交到朝廷手中??否则,一旦他人另起炉灶,抢先注册,反成侵权之罪。
这便是贾环早已预料的“倒逼之势”
。
地方豪强宁可主动交出技艺,也不愿被后来者抢占先机。
而朝廷,则在这场无形博弈中,不动一刀一兵,便将散落民间的“技术根脉”
尽数收归掌控。
然而,风暴之中,亦有暗流涌动。
钱益谦并未罢休。
他在家中召集门生故吏,冷笑道:“彼辈以为,一张纸就能锁住天下财源?殊不知,利之所趋,人皆可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