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皇修萧舒全集免费听 > 第1251章 将出(第2页)
第1251章 将出(第2页)
她没有抬头,声音平静如湖面。
我在她身旁坐下,随手拾起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致赵小兵叔叔”
,字迹稚嫩,出自孩童之手。
“这是他侄女写的。”
小梅轻声道,“今年十二岁。
她出生那年,赵小兵已经在雪地里躺了四十年。
但她爸每年清明都会对着北方喊一句:‘哥,娃长大了。
’”
我翻开信,里面画着一幅蜡笔画:一个穿军装的人站在雪山顶,脚下是一片开满紫晕花的草原,天上飘着彩虹。
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小兵叔叔,我梦见你回来了。
妈妈说你没死,只是走得太远。
我想告诉你,我不怕黑了,因为我听过你的歌。”
眼眶忽然发热。
“这三十七封信,”
小梅低声说,“每一封我都听到了回应。
不只是文字,还有写信时的心跳、停顿、擦掉重写的犹豫……它们都在告诉我:那些人,没有被遗忘。”
“那你呢?”
我望着她,“你有没有收到属于你的回音?”
她沉默良久,终于开口:“有。
三天前,一个老妇人来到腾冲古寺,跪在当年我父亲牺牲的地方,烧了一碗热汤面。
她说,她丈夫是那支失踪小队的炊事员,临终前一直念叨:‘要是那天多带一口锅,李队长就能吃上热乎的……’”
她声音微颤:“那一刻,我听见了父亲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求救,不是怨恨,而是笑着说:‘老张,面凉了也香。
’”
泪水终于滑落。
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冰冷,却又真实。
“你知道吗?”
她擦去泪痕,“我最近开始做梦了。
不是别人的记忆,是我的。
我梦见小时候父亲带我去河边抓鱼,梦见母亲给我扎辫子,梦见我自己站在阳光下大笑……这些梦以前从不会来。
因为我的心里塞满了别人的痛,没地方留给自己。”
“所以你现在……正在找回‘小梅’?”
“一点点。”
她微笑,“就像拼一幅碎了很久的图。
有些碎片找不到了,但新的也在长出来。”
我们并肩坐着,看云影掠过山谷。
远处传来钟声,是回声祠的新钟,由三百名倾听容器共同铸造,钟体掺入了他们的头发、指甲与一滴血,象征共感之誓。
突然,地面又传来熟悉的震颤。
这次不是脉冲,而是一种缓慢、沉重的节奏,仿佛大地深处有巨物翻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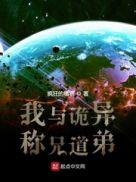
![总有偏执狂盯着我[快穿]](/img/3097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