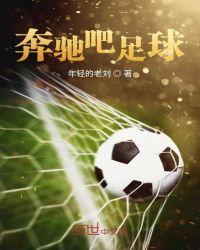笔趣阁>李珞应禅溪重燃青葱时代免费阅读笔趣阁 > 第863章 姐妹花大战(第5页)
第863章 姐妹花大战(第5页)
。
信纸泛黄,字迹由工整渐趋潦草,最后几封甚至有泪痕晕染的痕迹。
附在最后的便条上写着:
>袁老师:
>
>这些信是我丈夫生前写的。
他肺癌晚期时,每天写一封,说是要寄给女儿,可女儿早已失联。
他走后,我把它们锁在柜子里十年。
>
>上周听了分享会的新闻报道,我找到了女儿的联系方式。
昨天,我把信寄出去了。
>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读,会不会原谅。
但我知道,爸爸的爱,不该烂在土里。
>
>??一位母亲
>
>P。S。如果可以,请把这些复印件留在活动室。
也许,还能帮到别人。
袁婉青抱着信纸站在晨光里,久久不能动弹。
十点,她召集林晓彤、陈默和周叶,在活动室召开紧急会议。
“我们要启动‘信件复活计划’。”
她说,“收集那些从未寄出的信,无论是父母写给子女,还是孩子写给父母,哪怕是骂人的、哭诉的、道歉的,只要是真心的,我们都帮他们保存、朗读,甚至尝试送达。”
“我可以负责数字化归档。”
林晓彤立刻响应。
“我能联系社区广播站。”
周叶举手。
“我……”
陈默顿了顿,“我可以录音频旁白。
用我爸的声音做样本,合成一段温暖的开场白。”
袁婉青看着他们,忽然觉得这间小小的屋子,像一颗正在跳动的心脏。
下午三点,第一封“复活信”
被送来。
是一位七十岁老太太亲手写的,颤抖的笔迹布满整页纸:
>“儿子,妈妈当年把你送人,是因为穷得连米都买不起。
我不是不要你,我是怕你跟我一起饿死……这几十年,我每天烧一碗饭,摆在你小时候的座位上。
去年你妹妹告诉我你有了孩子,我偷偷去看过一次,长得真像你小时候……妈妈不求你认我,只求你活得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