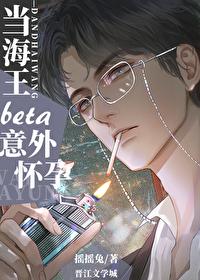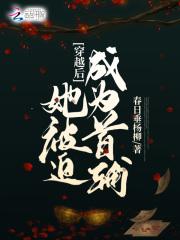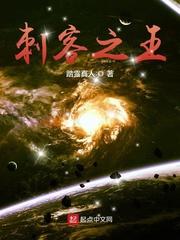笔趣阁>规则协议引爆中 > 神明创世(第1页)
神明创世(第1页)
魏商言深知,早期地球的狂热能量主要来源于板块内部的放射性元素衰变所释放的热量,以及火山喷发形成的甲烷、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当务之急是移动板块使地表温度下降,达成水蒸气凝结条件。
因此,魏商言果断操控地球板块抬起,他要利用山地海拔差异和增加的陆地表面积加速散热。
一方面可以固化二氧化碳降低温室效应。
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板块移动减缓地幔内部热量散发的速度。
仅是第一步,便消耗了他近三分之一的能量。
魏商言意识到,越大的动作消耗的能量越多,他必须严密计算以保证后期有足够的能量进行调整。
所以,在这一步之后他没再进行动作,而是静静等待时间的作用。
终于,地表在漫长的等待中,达到了温度的临界点。水蒸气碰上了空气中弥漫的尘埃,拥有了凝结核,很快,一场持续几个世纪的超级大暴雨降临,形成了地球上早期的海洋。
在这场闪电与雷暴激烈碰撞之间,魏商言敏锐的发现有机分子的形成,他知道,生命的雏形已经出现,他必须更加谨慎,因为往后任何一个操作都可能导致生命朝着不可控的方向改变。
魏商言将自己绝大部分神识投射在了这个有机分子身上。
它无比细微,但又无比坚强。它在地球初期狂暴的海洋表面之下静静生长、复制,从单螺旋结构逐渐演变成了双螺旋结构。
魏商言目睹了生命的诞生,这比任何宏伟的景观所带给他震撼都要来得巨大。
这些情感无关于规则、无关于人类的未来,而是对自然法则最纯粹、最崇高的敬畏。
此刻,魏商言感觉自己就像是发现新大陆的哥伦比亚,他屏息凝神,不敢错过一丁点画面。
逐渐的,他观察到生命雏形的发展有些受限,是什么原因让它大片死亡?魏商言赶忙查看所有环境因素。
就在生命所剩不多时,他发现,海洋中有机物质太少,能够给予生命新陈代谢的能量不多,他需要人工补充这部分能量。
于是,魏商言的眼光瞄准了一颗飞速驶向太阳系的彗星。
这是一颗包裹着大量水汽和有机质的冰彗星。
魏商言试探的用少量能量偏离彗星轨道,他的目标是使这颗饱含营养物质的彗星撞入地球海洋中。同时,他还要确保撞击点和撞击力度不得损伤这来之不易的宝贵生命,因此,他的每一次操作都只能是小小的微调。
在他的干预下,彗星拖着巨大而修长的尾巴划过天际,一头扎入大海,剧烈的碰撞给地球生命带来了新的惊喜。
真核生物,出现了。
一些大型细胞吞噬了小型细胞,但却没有消化掉小细胞,它们稳定的形成了「共生关系」。这一事件使得细胞的结构变得复杂起来,为单细胞生物向多细胞生物演变提供了基础。
魏商言自此以后没有再干预生命发展。
他深知,「神灵」角色是守护而非创造,也在此刻体会到「规则三:生命自有其意志」的含义,神可以创造摇篮,但无法决定生命的成长形态。
他也意识到,西奥多·克雷格想让他领悟的「规则的本质」的第一点内容:规则就像是物理定律,它规定了舞台的行为边界,但不关心舞台上的具体戏剧。
又过了相当漫长的时间,魏商言的意识随着恒星和行星的不断运动,在宇宙空间中孤单的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