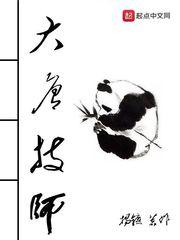笔趣阁>农家娘子改造日记 > 第五十九章(第2页)
第五十九章(第2页)
尹老先生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尹畔心有不甘,求知欲让他想弄明白父亲的意思,却又碍于情面不好再问,只好作罢。
另一头,还没走出尹家的邵堂却被一个管事模样的人叫住,“我家先生让我转达,学子的文章他细细看了,略有不足之处也勾选评写在旁。我家先生还说,学子若是此次中举,可再将文章送来,他很愿意指点一二。”
说着将东西交给他,邵堂打开一看,是自己当初耍小聪明让奉存新送来的诗赋文章,上头朱笔另批,写了不少。
邵堂按捺住雀跃谢过管事,却感觉脚下虚浮,一路走一路看,一时的失落害怕后又猛然的高高抛起,他此刻什么都听不见看不见,去到哪里也不晓得。
直到走到某一处无人的巷子里,踉跄了两步扶住墙,他才放声大笑起来,只觉得胸中多年块垒尽散,一扫而空,四肢百骸都说不出的轻松畅快。
心中只剩下一句话:他赌对了!
一旁有路过的人望来,暗骂了一句神经。
邵堂却根本不理会,笑过之后满心的欢喜,再不复此前惆怅低沉。
*
八月初旬,进入仲夏,檀州城内的金桂都爆开,满城飘着浓郁的香气,院子里的杏子树也终于熟透了,一场雨后掉在地上砸地到处都是。
冬云的活终于空下来,她学着朱颜只接一些顺手的活,空余的时间和朱颜研究剪纸灯笼的事,连棠姐儿喊她去钓螃蟹都不去,格外认真。
朱颜的本意是让她有个分心的事,没想到她钻研劲头十足,一日就能剪出十多种花卉人物的剪纸来,每日如此,原本只当是增加额外收入而入门的手艺,现在是越练越好,连朱颜都感叹她很有天赋。
这也让剪纸灯笼做出了第一个雏形。
样子出来了,不过问题却很多。比如麻纸染的红纸倒是可以用,但贴在灯笼上却和窗户上不一样,软塌塌的没有形状,花样单看起来复杂好看,可实际装上去却并不协调,甚至有点喧宾夺主的意思。
两人并不气馁,商量了问题出在哪里,继续投入心思钻研。
周娘子在初四的时候就回来了,脸色虽然透着憔悴,却带了笑容,还去将棠姐儿接了回来。
棠姐儿听说弟弟没事,本来被丢在四堂婶家里这么久的气也就消了一半,跟在冬云身后拿着小剪刀各种剪剪剪也玩得开心,另一半的气也就尽数消了。
等到八月十三,秋闱放了榜,第二日朱颜才想起要打听邵堂的事。
“他啊,落榜了。”奉存新睡了整整一日才起,又出去痛快玩了一日,等到放榜了也没去看,最后去书院拿东西时,听到其他学子说起的。
他考了两回,这回依然没有中,因而不打算在阳山书院继续耗下去,打算还是跟着尹老先去游学一阵,脚踏实地到处走一走,再细思读书的事。
郑学子中了举,四面都是恭喜声,谁也没把当初嘲讽他“上门女婿”的话再提,而郑学子也不在乎,脸上都是和气的笑接受了众人的恭喜。
“你平日里不见如何钻研,每月考试也不见得魁首,可这下了场见真章啊,你小子真是一鸣惊人!”有人笑,“反观隔壁升元县那个上月得了甲等第一的邵堂,当初那么风头浪尖,结果现在名落孙山了,真是丢人。”
“都是侥幸,不可议论,不可比较。”郑学子谦逊道。
“怕什么,咱们在这说说罢了。”另有人拍郑学子的肩膀,“咱们书院除了夏衙内,就你中了举人,我也觉得脸上有光,郑兄不得请咱们吃顿酒庆祝庆祝?”
郑学子平日里手面并不宽,又加上娃娃亲攀上了富庶的丈人,得书院不里不少人背后酸溜溜,将他喊做“倒插门”,因而郑学子很少和书院的同窗出门。
如今中了举人,再说不去的话就是过于孤傲,于是顺势点头招呼还算相熟的几人去吃酒。
奉存新得知此事后感到有些愧疚,总觉得是他送了文章到尹府,或许这样的举动没能得到尹先生的好感,反倒让邵堂在尹先生的眼里落了个钻营的形象。
现在回想起来,以邵堂的才学中举不过是囊中之物,可自己画蛇添足的多余举动扰乱了邵堂的心思,反受其累。
总之,奉存新觉得,邵堂此次落榜,自己多少有些责任。
当朱颜借着和周娘子说话的时候,向他拐弯抹角地打听,奉存新就含了些歉意:“是我的缘故扰了邵兄的心神,没能助他,反而带累了他落了榜,是我的错。”
朱颜松了口气。
她面上露出笑容:“奉学子不用自责,人各有命,这次没中代表他机缘没到,与你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