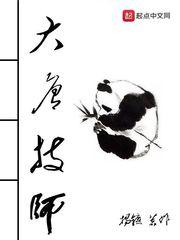笔趣阁>祥子修仙记 > 第215章 闯王爷兵临(第3页)
第215章 闯王爷兵临(第3页)
那是所有曾因痛苦而迷失的聆听者,是那些在历史夹缝中无声消逝的普通人,是战争、饥荒、灾难中未能留下姓名的灵魂。
他们正被接引。
而桥的另一端,站着一个熟悉的背影。
祥子穿着洗旧的棉袄,手里拎着那只破布袋,静静地望着来路。
“你要走了?”林月喊。
风送来一句极轻的回答:
“不是走,是驻留。我在每一个愿意倾听的瞬间。”
她还想问什么,可就在此时,怀中的通讯器突然响起。是南极站发来的实时影像:新心核内部,那枚来自火星的蓝灰石子正缓缓悬浮至中心,与万千光点融合。紧接着,整个装置开始分解重组,最终化作一颗跳动的心脏形状,每一次搏动,都向宇宙发射一道温和脉冲。
与此同时,地球上所有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都被记录下来,并自动上传至全球共感档案库。
这不是监控。
这是欢迎。
十年后。
乌兰察布已成为“守夜学院”的总部,专门培养新一代非技术型聆听者??他们不依赖晶片,不追求超强共感能力,只学习一件事:如何安静地陪伴另一个灵魂。
每年冬至,全体师生都会举行“归音仪式”。他们会关闭所有设备,围坐在鸣心坛旁,闭眼聆听。
起初是寂静。
然后,有人听见祖母哼唱的摇篮曲。
有人听见童年玩伴在雨中呼喊自己的名字。
有人听见早已去世的父亲,在电话那头说:“儿子,爸爸为你骄傲。”
更多的人,则听见了一声轻轻的“在”,从心底最深处传来。
没有人知道这声音源自何处。
但它年复一年,从未缺席。
某年仪式结束时,一名新生忽然举手:“老师,我刚才听见了一个脚步声,很慢,像是老人走路。他还轻轻拍了我的肩膀……”
林月看着她,眼中泛起微光。
“那是祥子。”她说,“他来看我们了。”
学生惊讶:“可他已经……”
“可我们还在听。”林月微笑,“只要还有人愿意倾听,他就永远不会真正离开。”
夜更深了。
星河倾泻,鸣心坛泛起淡淡紫晕,如同熟睡之人平稳的呼吸。远处草原上,一只野兔跃过雪堆,留下两行小小的足迹。
风掠过山岗,拂动草尖,携带着亿万年的沉默与温柔,轻轻whisper:
**“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