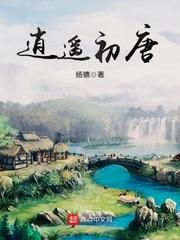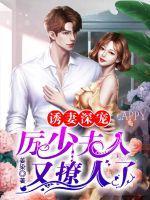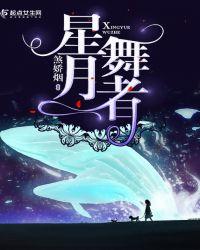笔趣阁>晋末芳华 > 第四百九十章 以诚待人(第2页)
第四百九十章 以诚待人(第2页)
“我父亲……他不是忠臣。”他嘶哑道,“他是刽子手。他下令沉湖那夜,亲手掐死了一名抱着琵琶不肯松手的小女孩。他说:‘音乐太美,容易蛊惑人心,必须斩尽。’可他自己……每晚都在梦里听见那孩子弹琴……他求我长大后替他赎罪,可我……我却把他的罪当成荣耀供起来……”
他瘫坐在地,泪水纵横:“我一直以为秩序高于一切,可现在我才懂,没有声音的秩序,不过是坟墓的规矩。”
数日后,他上表辞官,并公开焚毁家中所藏《禁语录》抄本。他在火堆前朗声道:“从今往后,我不再做‘正声’的奴仆,我要学着做一个会哭的人。”
这一幕被画工绘成《焚典图》,流传四方。
与此同时,拾遗者在整理新出土文献时,发现一部残卷名为《声世本纪》,作者不详,内容竟预言了林昭仪的一生??从山中逃荒女童,到执掌心岩的“听世之人”,一字不差。更诡异的是,书中最后一页空白,唯有几滴干涸的血迹,形状恰似一朵野花。
林昭仪看着那页,轻笑:“原来我的故事,早被人写过。可他们没写完??因为我还没活完。”
她提笔,在空白处补上一行小字:
>“未来之声,不在书中,而在路上。”
春去秋来,第三批共听坊启用,首次向囚犯开放。狱中设立“赎音室”,重刑犯可通过讲述过往罪行换取减刑。起初无人相信,直到一名连杀三人的江洋大盗在录音后崩溃痛哭,坦白自己幼年因饥饿偷粮,被族长当众鞭打至昏,从此恨极世人。他说:“我杀人时,耳朵里全是那天的鞭声。”
心理医者震惊:“原来暴力,也是一种失语。”
自此,“赎音制”推广全国,监狱不再是沉默的牢笼,而成了声音的疗愈之所。
而林昭仪并未止步。她发起“寻声万里”行动,派遣百支拾遗小队奔赴边疆、海岛、荒村,采集那些即将消亡的方言与古调。有一队深入西南群山,录下一位百岁老妪吟唱的《葬歌》,歌词讲述先民如何背井离乡,在战火中保存火种。当录音带回建康,学者才发现,那旋律竟与?湖底的《安民调》尾声完全一致。
“原来六百年前的乐师,唱的就是这首。”阿禾红着眼睛说,“他们不是凭空创作,而是传承。”
林昭仪仰望星空,轻声道:“声音,是最顽强的记忆。”
冬雪降临之际,《万声集》终卷完成。全书共九百卷,收录声音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七条,每一条皆附讲述者姓名、地点、心境注解。皇帝亲题书名,命铸青铜匣封存于太极殿地宫,另刻石碑立于?湖畔,上书:
>“此中有声,非乐非咒,乃民之呼吸,世之脉搏。后人若问何为太平,答曰:万人敢言,百音共生。”
开印当日,全国共听坊同步播放《无词之歌》??风过长城之声。那一刻,从岭南渔村到西域驿站,从东海孤岛到北疆哨塔,无数人停下手中活计,静静聆听。
一位老兵站在烽火台上,听着耳机中的风声,忽然举起右手,敬了个礼。
一位母亲抱着发烧的孩子,在陋室中轻声跟着哼唱。
一位年轻学子在灯下抄录歌词,写着写着,泪落纸上。
而在草原梦境中,那支由赤脚少女引领的队伍已绵延千里。她们不再是孤独奔跑的身影,而是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歌声震彻云霄:
>“我们回来了!这一次,永不沉默!”
林昭仪站在?湖畔的新悯乐祠前,望着湖面倒映的星河,忽然感到一阵奇异的安宁。她知道,这场变革不会一帆风顺,未来仍会有压制、有恐惧、有新的“声煞”诞生。但她也明白,只要还有人愿意倾听,还有人敢于发声,那声音的火种,就永远不会熄灭。
阿禾走来,递上一封信。是那位十二岁的聋女写来的,附着一幅画:太阳下,一个女孩张开双臂,脸上带着笑,周围画满了波浪线。
“她说,她‘听’到了光。”阿禾笑着说。
林昭仪抚摸着画纸,眼中泛起温柔的光。
“是啊,”她轻声说,“当我们真正学会倾听,世界就不只是用耳朵活着。”
夜风拂过,檐铃再响。
叮咚,叮咚。
像心跳,像低语,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
而歌声之外,大地深处,仍有无数声音在苏醒??在墙缝里,在古井底,在废弃的钟楼中,在母亲哄睡孩子的呢喃里,在少年仰望星空时的叹息里,在每一次不甘的呼吸里。
它们静静等着,等着一双愿意倾听的耳朵,一颗不怕疼痛的心。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事,从来不是呐喊,而是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