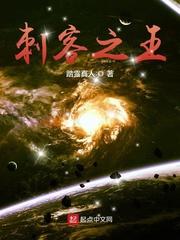笔趣阁>耳钉 > 萤窗雪案(第2页)
萤窗雪案(第2页)
“就这么定了,后天去检查。”夏云柏的声音打破了寂静,语气果断。
安欲殊只是极淡地应了一声,便径直转身上了二楼。
她在花满衣的房门外停下脚步,低着头沉默地伫立了许久,身影在廊灯下被拉得细长,最终才默然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国庆假期余下的三天,安欲殊与花满衣之间仿佛隔了一层薄纱。
她们默契地避开了所有独处的可能,连交谈都变得简短而克制。就连雷打不动的晨间阅读,也心照不宣地分开进行。
一个仍去万思书城,另一个,则转向步行街那家新开的书店。
日子无声流淌,开学如期而至。每日的接送,竟渐渐成了两人之间最心照不宣的尴尬时刻。
时光悄然滑过两周。这期间的周末,花满衣的身影总是匆匆。
一个冰冷的预感攫住了她,如果她和安欲殊之间,始终无人愿意率先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那么待到她离开之日,便是两人缘分彻底走到尽头之时。
她可以接受她感情永远得不到回应,也不愿坐视这样的结局。
所以,她决定绕开这堵沉默的高墙,从别处寻找突破口。
花满衣首先找到了较为熟识的曲晚。然而,当她说明来意后,曲晚显得颇为犹豫,并不愿轻易透露那些过往。
花满衣凝视着她,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我喜欢她,是认真的。”
她顿了顿,眼中泛起坚定的微光,继续说道:“如果过去困住了她,我就帮她解开。”
这句话带来的冲击让曲晚一时震住,但她毕竟见过风浪。在反复确认花满衣眼中那份不容置疑的真诚后,她终于沉吟着,斟酌词句,向花满衣透露了一些尘封的往事。
“我和小安,算来也就这两年的交情。知道的不算多。但你要明白,没人能责怪她不愿离开滁城……”曲晚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她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真正困住她的不是意愿,而是别无选择。”
“为什么?”花满衣轻声问。
曲晚叹了口气,吐出四个字:“因为她母亲。”
花满衣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有打断。
“再者,就是我和云柏他们了。”曲晚继续道,语气缓和了些,“我和夏家兄妹也不是本地人,小许是。你们现在住的那间酒吧,就是小许家的祖产。我们这些人,阴差阳错地,都成了她留在这里的理由。”
花满衣不解:“这之间有什么关联?”
曲晚的视线飘向虚无的远方,像是沉入了时光的深潭:“小许是留守儿童,由祖父母带大。十年前他父母工伤去世,老人用赔偿金开了家早餐店。可没等小许成年,老人也走了。正巧我和云柏来到这里,接手后改建成了酒吧。后来小安因母亲的事也流落到此。”
“那时她才十六七岁,整个人憔悴得像一张拉满的弓,仿佛随时都会断裂。”
两年前……
一只苍白的手推开厚重的木门,发出“吱呀”一声。
门口逆光站着一个身穿高中校服的女生。她扎着高马尾,身形单薄得像是风一吹就会倒,面色苍白,眼神里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憔悴与茫然,像一株濒临枯萎的植物,突兀地生长在这里。
角落里的夏榭屿抬起头,目光如冰冷的刀锋般在她身上扫过,带着毫不掩饰的戒备与审视,随即又低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