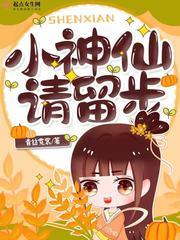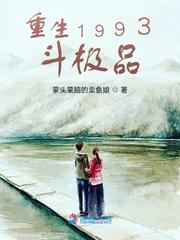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 第152章(第4页)
第152章(第4页)
“跟我走。”
江临舟指尖落下第一道声音。
接下来的许多天里,他们就一直以同样的方式上课。
没有固定的流程,也没有明确的进度表。
每天下午,江临舟推开琴房的门,唐屿已经在那里。
有时站在琴边,有时坐着翻书,有时只是静静听远处别的琴声落下来,像在等他。
他们从《唐璜的回忆》开始,
先讲故事,再讲结构,再讲角色,再讲每一句旋律的语气。
不是先练指法。
是先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江临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音乐不是从琴键开始的。
有一天下午快落日的时候,唐屿在琴上轻轻敲着那个二重唱的主题。
“你现在的右手比前几天好了。”
“少了浮躁,开始学会收着说话了。”
江临舟轻声“嗯”了一下,指尖还停在键面上。
唐屿又道:
“但你左手还是太实。她的犹豫还不够。”
江临舟抬眼,认真地听他说完。
唐屿没有在技巧上纠缠,而是将眼神落得很稳:
“你要知道她为什么会动摇。她不是傻,也不是天真。她只是看见了可能性。”
顿了一下。
“你如果不理解这个心情,你再怎么弹,都只是音。”
江临舟安静地点头。
那一刻他突然明白:
唐屿不是在教他怎么弹,而是在教他怎么理解音乐是靠人活起来的。
又过了几天,唐屿带来看似无关的书:
歌剧背景、十八世纪剧场文化、李斯特当年巡演的记录,甚至连那个时代的宗教与社会风气。
江临舟本以为那是理论书。
可唐屿只是翻到一小段,点给他看:
“你看这里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对无悔的人会感到恐惧?”
“音乐不是抽出来的。它跟人,跟时代,跟一个想法为什么会成立,都有关联。”
江临舟看着文字,忽然觉得曲子不是曲子了。它变成了世界的一部分。
有一天下课,他忍不住说:
“你知道的东西很多。”
唐屿没有否认,也没有谦虚,只是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