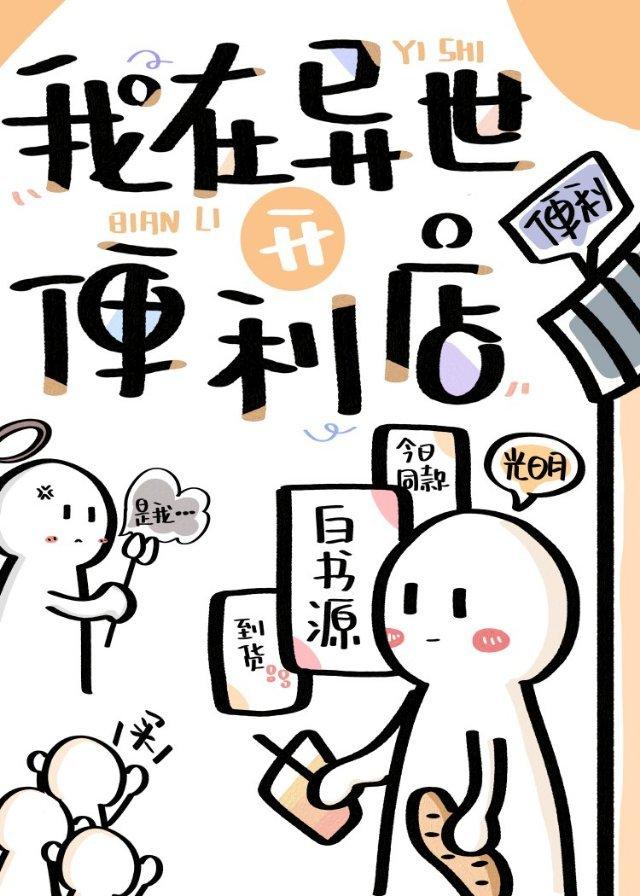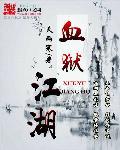笔趣阁>西游之浪浪山的金蟾子 > 第203章 金角银角 偷丹贼又来了(第1页)
第203章 金角银角 偷丹贼又来了(第1页)
这《龙象般若功》自然是金觉放到那里的,前世许多关于这葫芦爷的阴谋论,说什么‘盘古氏’、葫芦山山神转世什么的。
但在金觉的观察看来,这葫芦爷只是一个天生神力的凡人。想来只是机缘巧合,才会成为葫芦娃。。。
雪落无声,却压弯了浪浪山南坡那株百年老梅的枝头。一缕寒香浮在空中,像一句未说完的话,迟迟不肯落地。阿篱仍坐在赎言碑前,茶已凉透,杯沿上凝了一圈薄霜。她没有动,仿佛连呼吸都与这山、这雪、这碑融为一体。
裴昭也未离去。他靠在石栏边,手中摩挲着那支铜哨,哨身早已磨得发亮,映出他眼中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方才那一场逆钟鸣响,虽无声于耳,却震彻心魂。他知那钟声不只是唤醒记忆,更是在人心深处凿开一道裂缝??让光透进来,也让痛涌出来。
“你说,”他忽然开口,声音低得几乎被风雪吞没,“我们是不是太贪心了?既想让人说话,又怕他们说错;既要他们记住,又怕他们记恨。”
阿篱缓缓抬眼,望向他:“我们不是贪心,是不甘。林知远当年写下‘言亡于众声喧哗之时’,不是为了让我们沉默,而是提醒我们:真正的言语,从来不在人多嘴杂处,而在一个人独自面对良心时的那一声低语。”
裴昭苦笑:“可如今,连低语都被录成了曲子,在酒楼里唱给醉汉听。”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脚步声。不是急促,也不是轻巧,而是一种沉重的、带着镣铐拖地之声的节奏。两人同时转头,只见一名女子自山道缓步而来。她披着褪色的褐袍,脚踝上缠着铁链,每走一步,雪地上便留下一道血痕。但她走得极稳,目光直视前方,仿佛那双破旧的草鞋踏的不是积雪,而是千层冤狱。
阿篱站起身:“是你。”
女子点头,声音沙哑却清晰:“是我。我从京城来,走了四十九天。沿途每过一村,便有人递我一口饭、一碗水,只问一句:‘你还记得他们吗?’”
她从怀中取出一方布包,层层揭开,露出一块焦黑的木片,上面刻着三个字:**张元庆**。
“这是他在牢里用指甲刻的。”女子说,“临死前,他让我带出来,交给能听见的人。”
阿篱接过木片,指尖抚过那歪斜的笔画,仿佛触到了一个男人最后的体温。她闭目片刻,权杖轻点地面,井底回声再度泛起。这一次,不是碎片,而是一段完整的记忆??
画面中,张元庆蜷缩在潮湿的地牢角落,双手被铁链锁在墙上。他已瘦得脱形,但眼神依旧明亮。一名狱卒端来馊饭,低声说:“你何必坚持?没人记得你了。”
张元庆笑了笑:“我记得就够了。只要我还记得自己是谁,就没人能真正杀死我。”
那夜,他用指甲在木板上刻下名字,又将衣袖撕成条,蘸血写下遗书:“我不是求青史留名,只是怕后来者走我这条路时,连个脚印都看不见。”
记忆戛然而止。
阿篱睁眼,泪水无声滑落。她将木片轻轻放在赎言碑前,点燃一盏魂灯。火光跳动,映照出碑上新增的名字:**张元庆,年三十六,因揭发军粮贪腐案被构陷入狱,死于永昌七年冬。**
裴昭望着那簇微弱的灯火,喃喃道:“原来最勇敢的,不是振臂高呼的人,而是明知无人回应,仍坚持说出真相的人。”
女子忽然跪下,额头触雪:“我叫柳芸,曾是京畿道一名小吏。张元庆案发当日,我本可缄口,但我作证了。结果……我被革职,流放北境十年。如今赦令下来,我回来了,可家没了,亲人散了,连故乡的路都不认识了。”
阿篱扶她起身:“你回来了,就够了。名字有人念,魂就有归处。”
柳芸抬头,眼中含泪:“我想留下。我不想再逃了。哪怕只能扫地、守碑、点灯……我也要留在这里,替他说下去。”
阿篱点头:“那你便是守语人了。”
当夜,祠堂燃起长明灯。七十七名新晋静听者围坐一圈,无一人言语。柳芸坐在角落,低头看着自己残破的双手,忽然轻声道:“我有时候想,如果当初不说,是不是就能活得好一点?”
无人回答。
风穿堂而过,吹动檐下铜铃,叮咚一声,如泪坠地。
良久,阿篱开口:“你说出来了,所以你现在活着。如果你不说,你早就死了??不是身体,是灵魂。”
众人默然。可就在那一刻,每个人心中都响起一句话,不是谁说的,像是从地底、从风中、从彼此的心跳里自然浮现:
>“我没有赢。
>但我还在说。
>所以我还活着。”
这一夜,浪浪山的雪停了。月光洒落,照得赎言碑晶莹如玉。而远方,东海遗音洲的黑色石碑,那道裂缝竟又拓宽一分,从中渗出一丝微光,如同叹息。
与此同时,京城“舆情司”大堂内,灯火通明。
一位身穿紫袍的官员站在高台之上,手中展开一份奏报,声音沉稳:“陛下有旨:自即日起,全国推行‘言台积分制’。百姓在官方言台发表言论,可累积声望值,达一定等级者,可获免税、免役、甚至子女入仕优待。”
堂下群臣纷纷称善。
唯有角落里一名年轻文书官皱眉不语。他名叫陈砚,原是翰林院修撰,因私下传抄《禁史残编》片段被贬至此。他盯着那份政令,忽然冷笑:“这不是开放言论,是把说话变成生意。”
身旁同僚急忙拉他衣袖:“慎言!你忘了张元庆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