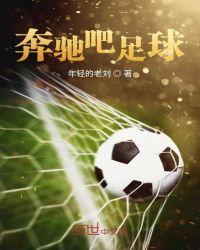笔趣阁>三国:从樵夫到季汉上将军 > 第155章(第2页)
第155章(第2页)
是夜,他独坐茅屋,提笔续写《牛公言行录》:
>“为将者,不在斩将夺旗,而在使百姓无需上阵亦能安居。
>为政者,不在威仪赫赫,而在使孩童读书时不闻哭声。
>真正的强盛,不是城池坚固,甲兵犀利,而是人人知耻且格,家家有余粮,户户点灯读书。”
忽闻叩门声。开门见一白发老妪,拄杖而立,身后跟着个十岁幼童。
“药翁……”她哽咽,“我夫君当年蒙您救活,临终前嘱咐我,若有一日南中再乱,请务必带孙儿来找您。”
牛金扶她进屋,问:“如今太平,何来再乱之说?”
老妪从怀中取出一块残破铜牌,上面刻着“魏谍”二字:“昨日市集,有人用金饼买粮,却不食不用,只问哪里屯兵最多、何处道路易行……我认得这牌子,是我儿战死时从敌尸身上搜出的。”
牛金接过铜牌,指尖微微发颤。他知道,魏国从未真正放弃南中。
翌日,他下令重启“警哨制度”,恢复孩童演练暗语。又派猎户伪装商旅,深入交州边界探查。十日后,密报传来:确有魏国细作混迹商队,携带大量黄金,意图收买部分边缘部落首领,许诺事成后封王授地。
牛金冷笑:“他们以为,只要钱够多,人心就能买走?”
他不动声色,命人在市集设“假仓廪”,堆满草袋冒充存粮,并散布谣言:“南中即将征兵万人北伐,急需调粮。”果然,数日后一名“商人”趁夜纵火,欲烧毁“粮仓”。埋伏已久的守耕队当场擒获,搜出身契、密信若干,连同口供一并送往成都。
诸葛亮点评此案,只写八字:“民心如土,不可轻辱。”
风波渐平,然牛金心知隐患未除。一日黄昏,他独自登临义州最高山峰,俯瞰千里沃野。夕阳如血,洒在层层梯田之上,宛如披金戴甲的士兵列阵待发。
孟琰寻来,见他伫立风中,便轻声道:“老师可是忧虑未来?”
牛金点头:“和平太久了,人们开始忘记代价。你以为‘耕贤榜’能永远激励人心?若有一天,年轻人觉得种地无趣,当兵才有荣耀呢?”
“那便教他们明白,真正的荣耀不在战场斩首多少,而在田里养活多少人。”孟琰坚定道。
牛金看着他,忽然笑了:“你比我当年懂得多。”
回到山下,牛金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命人将自己居住多年的“济世庐”拆除,原址改建为一座学堂,名为“守心书院”。
院中立碑,刻其亲撰铭文:
>“吾非圣贤,但求无愧。
>少年仗剑,以为杀戮可定天下;
>中年执犁,方知耕耘始得太平;
>暮年归静,唯愿后来者不蹈覆辙。
>此地不祀我名,只传一念:
>心中有田,处处皆可生根。”
书院落成当日,牛金亲自授课,题目为《为何我们要读书》。
台下坐满少年,最小者不过六岁。
他说:“你们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发财,不是为了欺负别人,而是为了看清这个世界的真实模样。比如,为什么有人宁愿饿肚子也要偷懒?因为没人教他劳动的意义。为什么有人拿钱就能背叛家乡?因为他的心里没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
他停顿片刻,声音低沉下来:“我见过太多人,一开始是为了吃饱饭而打仗,后来打着打着,就忘了为什么要打。最后发现,打赢了,也没人吃得上饭。”
孩子们静静听着,眼中闪烁着光芒。
课毕,一个小女孩举手:“牛爷爷,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牛金微笑:“回家告诉父母,明天一起去插秧。然后记住??你弯下的每一次腰,都是在为这个国家筑一道墙。”
三年光阴流转。南中愈发富庶安定。而此时,北方局势再度紧张。司马懿病逝,其子司马师掌权,厉行改革,整顿军备,虎视西南。
朝廷再次征召牛金入朝辅政,诏书连发三道,皆被婉拒。最后一次,使者带来诸葛亮亲笔信:
>“孔明手书:
>吾兄若再推辞,则恐后继无人。
>我已病卧五丈原,风寒入骨,咳血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