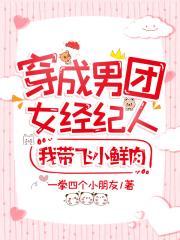笔趣阁>稚御山河 > 第三十三回 民谣惊殿揭苛吏影 诗笺藏讽触龙颜(第3页)
第三十三回 民谣惊殿揭苛吏影 诗笺藏讽触龙颜(第3页)
他抬眼扫过脸色骤变的钱为业,继续道:“这张翠喜生得貌若天仙,一双眼含情带露,唱起《霓裳》片段能让楼里客官忘了举杯,杜之贵为赎她,竟一口气花了三万两纹银!可他一个四品太守,一年俸禄撑死不过两百两,这三万两是刮了多少百姓的粮饷,才凑出来的?更可气的是,他赎了人却不敢留,转头就把张翠喜献给了桂宁侯,就为了靠这层关系,换个扬州刺史的前程!”
“陛下您再细品歌谣里的后半句,”齐王话锋转向御座,语气沉了几分,“‘田埂草枯盼雨露,暖阁笙歌日头低’——百姓在地里饿肚子盼救济,他却拿民脂民膏买歌女讨好权贵,这样的人要是真去了扬州,江淮的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这歌谣总不是臣弟编出来的吧?”
齐王目光陡然转向钱为业与朱启建,语气带着不容回避的追问:“钱尚书、朱大人,方才你们说百姓证词是‘挑唆’,诗句是‘用错典故’,如今这歌谣、这三万两赎金献歌女的事,二位又有何高见?总不能说,这也是有人故意编造,栽赃杜之贵吧?”
朱启建瞬间慌了神,深绯色官袍下的手止不住地哆嗦,眼神直往钱为业身上瞟,嘴唇动了好几下,才挤出几句断断续续的话:“这……这歌谣说不定是……是市井谣言,当不得真!张翠喜……谁知道是不是同名同姓……”话没说完,自己先没了底气,声音越说越小。
钱为业心里早乱成了麻,指尖攥着玉笏的力道几乎要将其捏碎,可面上仍强撑着沉稳,忽然灵光一闪,急声道:“陛下!齐王殿下!这其中定有误会!杜之贵献歌女给桂宁侯,臣倒是略有耳闻——可那不是讨好权贵,是桂宁侯府中宴客缺乐师,杜之贵是为了助侯府‘礼待宾客’,才举荐了张翠喜!”
钱为业额角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滑,声音里带着几分慌乱的辩解:“至……至于三万两,臣是真不知道!不过我朝各地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商户们感念官员办实事,每年会凑份‘敬礼’,钱数可多可少。说不定这赎金,是城阳商户们自愿凑的,并非杜之贵挪用公款啊!”
他这话刚落,齐王当即笑出声,语气里满是讥讽:“哦?照钱尚书这么说,城阳的商户倒真是大方!一出手就是三万两给官员赎歌女,那他们每年凑的‘敬礼’,岂不是得有几十万两?可城阳就那么些商户,一年到头赚的钱加起来,能不能有几十万两都难说——您这是把满殿同僚都当傻子,还是觉得陛下好糊弄?”
这话戳中了要害,钱为业瞬间哑口无言,连先前强撑的沉稳都绷不住了,站在原地手足无措,殿内的议论声也越来越大,显然没几个人信他这套说辞。
齐王话锋一转,目光扫过殿内,语气里多了几分探究的锐利:“各位大人不妨再想想——桂宁侯此次是奉陛下旨意,以钦差身份巡视燕蓟之地,按规矩该从洛京往北走,先到燕京,再查周边州郡。可他却绕了个大弯,直接去了东边的城阳,这难道不蹊跷?”
他顿了顿,继续道:“燕蓟之地是边境要地,陛下最是看重,桂宁侯放着要紧的差事不管,偏要先去城阳,难不成城阳有他的亲戚要探望?还是说,他早就知道杜之贵会送张翠喜给他,特意绕路去‘接人’?若真是这样,那杜之贵献歌女、桂宁侯徇私,就不是巧合,而是早有勾结!”
这番话把“桂宁侯绕路”和“献歌女”的事串到一起,瞬间让殿内气氛更紧张——钦差擅改路线,本就是大罪,若再牵扯出勾结地方官,性质就更严重了。钱为业听得脸色铁青,却一句话也接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齐王把这桩事越挖越深。
齐王见向昚面露困惑,连忙收了厉色,放缓语气,用最直白的话解释:“陛下,简单说就是——桂宁侯本该去北边查边境,却特意绕路去城阳,就是为了收杜之贵送的歌女张翠喜;杜之贵花三万两买歌女送人,这钱十有八九是从百姓身上刮来的;他们俩一个受贿徇私,一个搜刮民脂,要是不查,以后官员都学着这么干,百姓就没法活了!”
向昚听完,眨巴了两下眼睛,脸上还是没多少怒气,拍了拍御案,脸上露出几分“恍然大悟”的神情,语气带着孩童般的直接:“嗨,这有啥难的!既然弄不清楚,那就把杜之贵和桂宁侯都叫回来问问不就完了?他们俩当面说清楚,是啥情况不就知道了?”
说罢,他转头对着殿外高声吩咐:“来人!派两个善差去!一个去扬州,把刚上任的杜之贵给朕叫回来;另一个去燕蓟之地,找到桂宁侯,让他别巡了,赶紧回洛京!”
向昚挠了挠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皱着眉道:“可把人叫回来,总得有人审吧?总不能让朕来审案吧?朕哪会这个!”说着,他转头看向孙幽古,语气带着依赖,“孙相,你觉得谁来审合适?”
孙幽古心里暗叹一声,知道躲不过,只能躬身回话,语气依旧是不偏不倚的稳妥:“陛下所言极是。审案需得公正严谨,臣举荐由齐王殿下任主审——殿下既查了城阳之事,掌握的线索最详,且心系民生,定能秉持公允;再让吏部钱尚书任副审——钱尚书熟悉官员考核制度,可从选官流程上辅助查证,二人相辅相成,既能查清案情,也能让朝野信服。”
这番安排看似合理,实则还是“三不沾”——让查案的齐王主审,让保杜之贵的钱尚书副审,既没偏向任何一方,也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免得后续出了问题牵连到自己。
齐王闻言,眼底飞快闪过一丝算计,随即上前一步,语气带着几分“公允”的提议:“陛下,丞相举荐臣与钱尚书审案,臣无异议。只是此案还牵扯到吏部考课之事,朱启建大人身为吏部四品官员,平日里也参与官员考评,不如也让他一同加入审案,多个人多份参考,也能让案情查得更细致周全,您看如何?”这话看似是为了“周全”,实则是捏住了朱启建的软肋——他先前多次为杜之贵辩解,如今让他参与审案,既是把他放在明处,让他不敢轻易偏袒,也能借他的身份牵制钱尚书,免得两人私下串通遮掩。
向昚听完,没多想便点头:“行啊!多个人帮忙也好,就按齐王说的办!你们三个好好审,早点把事儿弄明白!”向昚伸了个懒腰,摆了摆手道:“没别的事就退朝吧,朕还得去看看新驯的鸽子。”
众官员连忙躬身,齐声三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随后叩首起身,依次退出大殿。皇帝率先起身,在侍卫的簇拥下往寝宫去了,龙袍下摆扫过金砖,留下一串轻响。
承光殿内很快只剩下齐王、孙丞相、钱尚书与朱启建四人。殿外的铜铃还在风里轻晃,殿内的香炉青烟却已散了大半,气氛瞬间沉得像结了冰。
钱尚书攥着玉笏,指节泛白得几乎要嵌进玉里,先是瞥了眼始终沉默的孙丞相,才转向齐王,语气慢悠悠的,每个字都藏着暗刺:“齐王殿下今日在殿上如此‘尽心’,连歌谣、歌女的琐事都查得一清二楚,倒真是比吏部还关心地方官的‘德行’。只是审案讲究‘证据确凿’,殿下可别为了‘查案’,反倒落了个‘捕风捉影’的名声,让陛下觉得殿下心思太重啊。”
这话明着是提醒“讲证据”,暗里却在影射齐王借案争权,还把“陛下的看法”搬出来施压,试图拿捏齐王的顾忌。朱启建听出了弦外之音,忙不迭点头附和,声音都带着颤:“钱尚书说得是!殿下一片苦心我们懂,可……可桂宁侯那边毕竟是皇亲,真要是没查明白就惊动了他,怕是会让陛下为难啊。”
孙丞相依旧没接话,只抬手摸了摸颌下胡须,目光在三人脸上转了一圈,眼神里辨不出喜怒,活像个置身事外的看客,唯独指尖偶尔摩挲玉笏的小动作,泄露出他并非全然无动于衷。
齐王却笑了笑,绯色亲王袍在残烛下晃出冷光,语气坦然得没半点避讳:“钱尚书放心,本王只查案情,不问其他。若是杜之贵、桂宁侯清白,本王自然会还他们公道;可若是真有贪腐徇私,就算是皇亲,也不能坏了陛下的规矩——这难道不是为官该做的?”
他话锋顿了顿,目光落在钱尚书紧绷的脸上,又添了句轻描淡写的话:“对了,方才忘了说,本王的亲信在城阳暗访时,还查到杜之贵任内,曾给洛京某位大人送过三箱‘漕运特产’,听说箱子里装的不是粮米,是成色极好的东珠。至于那位大人是谁……审案时,或许能让杜之贵好好说说。”
钱尚书的脸“唰”地一下白了,垂在袖中的手猛地攥紧,连呼吸都漏了半拍——他哪里会不知道,那三箱东珠,正是杜之贵去年托人送到他府里的“谢礼”。
齐王看着他骤然失色的模样,眼底笑意更浓,却没再往下说,只转身朝殿外走:“明日辰时,大理寺公堂见吧。钱尚书、朱大人,可别迟到了。”
脚步声渐远,钱尚书才扶着案几勉强站稳,额头上的冷汗早已浸透了官帽衬里。孙丞相这时才缓缓起身,看了他一眼,语气依旧平淡:“钱大人,明日审案,可得想清楚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说罢,也不等钱尚书回应,便拂袖而去。殿内只剩钱尚书与朱启建两人,烛火噼啪作响,映着两人各怀鬼胎的脸——谁都清楚,明日的大理寺公堂,绝不会只是审杜之贵那么简单。而远在扬州的杜之贵,还不知道自己刚坐稳的刺史之位,早已被洛京的风波缠上,只等着他回京,便要卷入一场滔天漩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