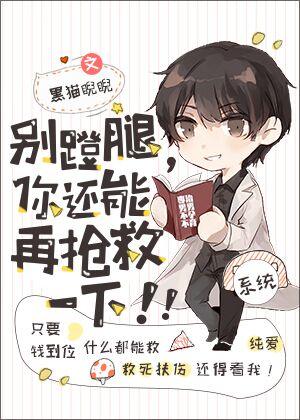笔趣阁>娘子何日飞升 > 230240(第29页)
230240(第29页)
“宋凛生、宋凛生!”
敕黄这回是听了个真切,他心下一惊,来不及思考什么,便随着耳间银环的叮铃声骤然冲向榻前,两手将睡梦极不安稳的女子揽起。
他臂膀上的银钏随着动作的晃动,发出阵阵混乱的声响。
一时间,殿内鸣声不止。
“烧火棍!你醒了?”
敕黄语带关切,同时掺杂着难以抑制的焦灼,似乎等这一刻已等了不知多久。
如今了无生气地靠坐在敕黄怀中之人,正是文玉,其煞白的面庞忽明忽暗、毫无血色,即便是在前者的阵阵呼喊中,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文玉犹疑的目光扫过四周,似乎仍沉浸在什么当中无法挣脱,三分茫然七分无措令她一时间说不出什么更多的话来。
并不理会敕黄的呼唤,文玉只一遍又一遍地低声寻觅着,似乎在执着于寻觅某种回答。
——是宋凛生,百年来她曾无数次梦见过的宋凛生。
如同从前的每一次梦醒,她也总是这样地低喃。
“宋凛生……”
待敕黄听清她口中所言,不免心忧却又无可奈何,“别念了,他不在。”
言罢,不知是想到了什么,敕黄竟有几分负气,“那个凡人不是死了三百年了?”
他有些不平,亦有些疑惑。
不过是一个凡人,竟也值得她挂心百年?
如今来看,当初纵她下界也不知是对是错。
文玉闻言一怔,僵硬地抬首循声往上看去。
圆润可爱的犄角自敕黄蓬松的发间生出,随着他言语的动作,双耳坠下的银环此刻正叮当作响。
窗前半开了灵智的草木躬身探头进来瞧她,屋檐上的脊兽一则是股脑儿地围在敕黄身后,叽叽咕咕地不知在说些什么。
从前与眼下重叠,虚幻和现实交织,文玉脑中一痛,终于明白过来——
此处是东天庭,春神殿。
她从幽冥府请辞,如今不再是轮回司往生客栈的孟婆,自然该回春神殿的。
春神殿并非梧桐祖殿,如今亦不是三百年前。
旧梦一场,猝然梦醒以后,她又该去哪里寻宋凛生呢?
精心留存的寿元枝也已随风消散,眼下她手上哪里还有一星半点与宋凛生有关的线索。
原来到头来,仍旧是空花阳焰、一枕槐安。
文玉垂首不语,只怔忪地凝视着自己空无一物的掌心,其指尖蜷缩间,竟只余下一片虚浮。
宋凛生说的没错,世间万物,仅凭人的双手能把握住的……并不多。
那她呢?她已经羽化飞升、并非凡人,可为什么仍然会如此无力。
同样的问题,她已经反复拷问自己三百年,却始终求不得一个确切的答案。
“烧火棍?烧火棍!”
敕黄见势不好,原本平整的眉头不自觉向内拢起,他收住话头,不再玩笑。
“文玉,你别吓我,我方才全是胡言乱语的,文玉?”
难得他如此正经地称呼自己的名姓,文玉自茫然中抬头,视线一点点在敕黄身上聚焦。
一向潇洒肆意的敕黄,如今望向她的牛眼中竟泛着难掩的水光。
她也不知躺了多久,惹敕黄担心了罢。
文玉心头一紧,原本还有些伤怀的心绪亦只能强压着,开口间便改换成云淡风轻的做派。
“大黄!”
她腾地坐起身,抬手揪住敕黄的牛角,煞有其事地训道:“知道胡言乱语还不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