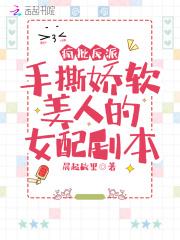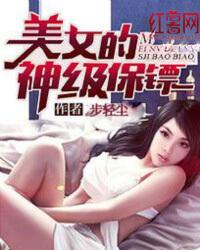笔趣阁>大唐之最强皇太孙 > 第2297章 主宰(第2页)
第2297章 主宰(第2页)
半年后,长安城南郊新建了一座圆形议事堂,名为“疑庐”。其形制仿古,无主位,百席环列,专供“初始审议团”使用。堂外立碑,刻有小禾亲笔所书十六字:
**“疑而后信,问始为安;非求定论,但守真言。”**
此时堂内正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辩论:是否应全面开放“记忆档案”的公众查阅权限。
支持者认为,唯有让每个人都能查看自己从小到大的心理评估、课堂表现记录、社交关系图谱,才能防止隐形规训;反对者则警告,过度透明会导致人际关系崩解,人人自危。
争论激烈,持续七日未决。
第八日清晨,一位老妇人拄拐入场,身穿粗布衣,脚踩草鞋,自称来自河东郡某山村。她不会写字,但带来一段录音,播放后全场寂静。
那是她十六岁的孙子在“认知矫正中心”最后一段独白:
>“我说老师讲的‘民族团结史’漏掉了我们村被征地时的抗议,就被送来这里。他们让我每天抄写‘我必须尊重官方叙事’一百遍。第七天,我抄着抄着哭了。辅导员说:‘别感情用事,理性点。’可我想不通,为什么不能一边理性,一边伤心?”
老妇人颤声道:“我不懂什么叫‘叙事建构’,我只知道我孙子出来后,再也不肯叫我一声奶奶。你们要透明,我赞成。但请告诉我,怎么把孩子的眼泪也变成档案的一部分?”
全场落针可闻。
最终,审议团以微弱多数通过提案,但附加一条:所有档案公开前,必须由“情感标注小组”添加背景注释,说明每一份记录背后的生活情境??譬如某次考试失利,是因为学生父亲病逝;某条负面评价,源于教师个人偏见。
这项制度后来被称为“泪痕标注法”,成为全球首个将情感维度纳入公共信息管理的实践。
***
与此同时,小禾已悄然抵达北方边境。
此处有一座废弃的烽燧台,原为军事?望所,如今被一群退伍老兵改建为“自由思辨营地”。他们不分昼夜地讨论:国家为何总在和平时期宣扬战争威胁?边境冲突的新闻报道是否存在模式化渲染?甚至有人提出:“我们是不是被训练成了永远准备打仗的民族?”
小禾混迹其中,化名“阿禾”,担任炊事员。她每日挑水、劈柴、煮粥,偶尔在晚饭后讲一个小故事??关于一个孩子如何通过测量影子长度证明太阳并不绕地球转,却被教会判为“动摇宇宙秩序”。
渐渐地,老兵们开始主动找她聊天。
“你说,我们这些年冲锋陷阵,到底是为了保卫国家,还是为了维持一种‘必须时刻备战’的集体心态?”一名独臂老兵问。
小禾反问:“那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以前觉得是。”他苦笑,“现在看新闻,发现我们的事迹被剪辑成短视频,配上激昂音乐,在学校里循环播放。孩子们看完就喊‘打打打’。可战争不是游戏,牺牲也不是表演。”
小禾点头:“最可怕的不是谎言,而是把真实的事包装成另一种意义。”
当晚,她在笔记中写道:
>“当爱国成为仪式,战士就成了道具。
>当牺牲被反复消费,鲜血便失去了温度。
>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颂歌,
>而是对荣耀保持警惕。”
几天后,营地迎来一位特殊访客??余仲文之子,自称“归真新一代领袖”。他带来一台投影仪,在夜幕下播放一段视频:画面中,数十名青少年跪拜于山洞前,齐声诵读《归真辑录》中的段落,内容竟是对“全民共治计划”的数据分析,指出其投票权重偏向城市居民,农村意见易被稀释。
“看!”青年高呼,“连你们推崇的民主,也是精密计算过的控制!”
老兵们骚动起来。
小禾站出来说:“你说得对,制度有缺陷。但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让我们跪着寻找真相?”
青年冷笑:“至少我们诚实??我们承认自己需要信仰。而你们呢?用‘科学’‘理性’‘程序正义’掩盖权力分配不公,这才是最深的欺骗!”
小禾静静地看着他,忽然笑了:“你知道陈玄最后悔什么吗?不是写了《黑暗自白》,而是以为只要揭露谎言,世界就会变好。但他忘了,人不仅需要真相,还需要希望。你们提供希望,但我们不能因此放弃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