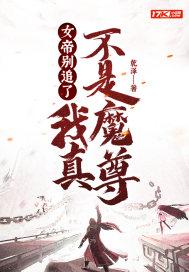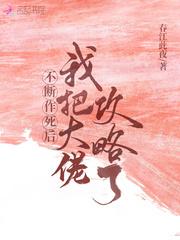笔趣阁>大人冲冲冲 > 第172章 三临边城(第2页)
第172章 三临边城(第2页)
“虽然两人的气息和下意识的反应完全不同,但是他们运用的规则之力确是同本同源的。”李袖招的语气中也有一丝罕见的不确定,“也许正是同一个人,而我们之前的猜测是错的。”
如果龙阳君被确定了,那么云霄就可以被排除怀疑了。
林小暖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袖招,这次前去西北境边关我陪你一起。”
“好。”
第二日,早朝散朝的时候,一众大臣都还在啧啧称奇。
昨天小燕公还坐在高台上,明明白白地反对大司礼,不让大司礼去西北境边关,结果今天一上朝,小燕公就宣布了要跟随大司礼一起前往边境的消息。
众人恍然大悟,都“明白”了小燕公的用意。
感情自家陛下是怕大司礼出事,而不是真的跟大司礼意见相左啊,要不然怎么会决定亲自跟着大司礼前往西北境边关?
燕国的军事实力足以对敌军形成碾压,更别说西北境边关此时还有一位云霄上将军坐镇,林小暖此行还是有足够的安全保障的,这是诸位大臣们的共识。不过共识也好,理解也罢,上朝的时候,一群人还是得不停劝阻林小暖。
什么“陛下多考虑一下燕都的情况”,什么“陛下不要只身犯险”林小暖在武阳宫高台上干坐着听一群大臣唠唠叨叨了半天,最终还是忍不住“三急而走”,在外面一直躲到中午,算算时间也拖到各位大臣大概等的不耐烦想回去的时候了,这才大摇大摆赶回来宣布散会。
小燕公十七年,九月,王出征,自燕都行,将战于萤川。
林小暖这次前往西北境边关是一场正式出行,正式就意味着仪仗队、军队护卫,随从千百人
也就意味着在行军上花费的时间会拉的很长。
还没到西北境边关的时候,林小暖就接到了战线前方斥候的消息,因为她的出行大张旗鼓,秦军也很快得知了消息,秦王也在加紧向萤川这边赶来。
这是一场国君与国君的会面,新旧霸主之间的碰撞。
出行没几日,前方战线有新消息称魏国和楚国似乎也在纠集军队,打着“天下有乱,助燕勤王”的旗号也准备加入这场战斗。
世人就是这样,最喜欢做的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林小暖心底通透,觉得这两个国家一定是闲的急了,纯粹跑来凑热闹的,出力可能不会出多少,现在估计都打着小算盘怎么敲燕国一笔油水,但面子还是要给,便给两国国君各发了一份感谢函,几千字洋洋洒洒赞美,就是不说物资分配问题。
半个月后,林小暖的队伍到达锦官城,再向前就是西北境边关了。
下榻锦官城的当日,传信人从西北境边关来,向林小暖当庭传达了秦军新发的“萤誓”,又称“讨燕檄文”——因为燕国多年裹挟周天子镇压诸侯的“暴政”,以及十六年前来犯秦国边境掳走公子袖招至今仍未归还的行为,秦国决定对这不仁不义的君主带领下的燕国宣战,而且现已纠集了三路大军,正在萤川处严阵以待。
传信人还告诉了林小暖一个小道消息,西北境边关的将士们此时正在与敌军打口水仗,“战况激烈”。
自从林小暖十几年前在西北境边关开了口水仗的先河,不知怎么的就变成了现在燕军的传统,如果两军对战,一军提出了先来一场骂战的请求,那么这方提出骂战要求的十有八成就是燕军,这已经是天下皆知的事实,也是燕军的特色。
不过,接到这样的消息后,随行的学士、军师们都一片哗然。
秦国给出的两个罪名中,其中,“暴政”一事纯属虚构,“掳走”怪罪更是强词夺理——李袖招留在燕国一事李氏部族都不追究了、秦国的追究是完全没有理由。
两个“莫须有”罪名,只能传递出一个表态,那就是秦国是铁了心要和燕国开战。
林小暖怀疑秦军因为长期的封闭,已经和整个中原脱节,导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目前中原最强的军事力量到底在哪里。
她坐在软轿上听传信人念消息的时候,一手扶额。
忽然感觉她自己像一个被小孩子挑衅了的大人,面对对方以“莫须有”罪名加注的出征,她没有愤怒,反而更多的是无可奈何。
怎么就非要打架呢?和和气气一起发展不好么?
而且还只打燕国就因为燕国比相邻的魏国和楚国都小么?能不能多了解一下情况再挑对手啊,你们这么赶着来送我真的很难办啊
况且,这次从边境送回来的不仅仅只有对面的“檄文”,还有我方已经掌握的对面的三军配置、具体人马、地势以及可能的作战计划和初步应对假设等等一连串内容。
因为三年大旱、三年大寒而导致的天下无战事,燕国本来跟随着“联合国大军”四处征战的老兵油子们现在全部驻守在燕国的边关,每天吃吃睡睡钻山下海训练都无聊的要死,现在看到秦国的进犯,简直跟狼闻到羊膻味一样!
搞侦查的恨不得将秦国领兵将军内裤是什么颜色都搞清楚;搞防御工事的恨不得将燕军这边的阵地武装到如铁桶一般;搞作战参谋的恨不得将战事结束后年之内怎么防止再犯的方法都考虑清楚可以说,这群“磨刀霍霍”、“饥渴难耐”的边境战士们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像上一次那三位士兵一样冲上去“包抄”秦军,原因只在于林小暖这边还没松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