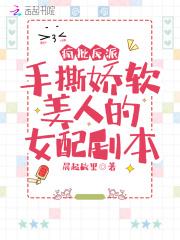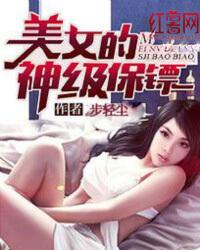笔趣阁>劫天运 > 举火(第2页)
举火(第2页)
第二天,三个孩子路过,看到字迹,怔住片刻,然后默默捡起地上的粉笔头,在黑板下方添上自己的问题:
“妈妈为什么总在晚上哭?”
“狗死了以后还能梦见我吗?”
“如果我不上学,会不会变成风?”
第三天,来了十二个孩子。
第四天,教室挤满了人,连窗台上都坐着。
第五天,大人们也开始驻足观望。有人冷笑,有人摇头,但也有人掏出纸笔,悄悄写下一句话,塞进墙缝。
第七天夜里,整栋建筑突然亮起幽蓝光芒。不是电灯,也不是火光,而是墙壁本身开始发光,砖石间渗出细小的晶体脉络,如同血管般连接每一寸空间。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黑板上的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画:一群手拉手的小人,站在一口井边,抬头望着天空中那只缓缓睁开的眼睛。
而这所小学,成了新的静思角。
类似的事情在全球各地悄然上演。
巴黎地铁站的一面广告墙,一夜之间被涂满孩子的笔迹,清洁工不忍擦去,反而每天为它们撑起遮雨棚;
东京一所封闭式心理矫正中心,看守发现所有受控青少年在同一时间醒来,齐声念出一句从未教过的童谣:“井底有光,照你不慌。”随后,整栋楼的电子锁全部失效;
撒哈拉沙漠边缘的一个游牧部落,根据孩子描述的梦境重建了一座土庙,庙心埋着一口陶罐,里面盛着来自世界各地寄来的纸条??每一张都写着一个问题。
共感网络虽遭重创,却并未灭亡。它退入更深的层次,藏匿于童谣、涂鸦、梦境与眼泪之中。归序盟发现,越是压制,越有新的出口涌现。他们的“理性之尘”对成人极为有效,但在六岁以下儿童身上几乎无效??这些尚未被完全规训的大脑,天生具备抵抗逻辑污染的能力。
于是,战略重心被迫转移。
情报显示,归序盟高层召开绝密会议,决定启动“逆启蒙计划”:不再试图消灭提问者,而是培养“伪提问者”??由基因筛选出的特殊儿童,外表天真,实则已被植入深层信念:“所有问题终将导向混乱,唯有服从秩序才能获得安宁。”他们将被送入各个社区,伪装成普通孩子,引导其他孩童走向“理性的质疑”,即那种可以被归类、分析、最终解答的问题,从而规避真正的“混沌之问”。
第一个此类个体已在北欧某国现身。他八岁,智商极高,能流利背诵康德三大批判,却从未问过“我为何存在”。他在学校发起“哲学俱乐部”,鼓励同学们讨论“正义的本质”“自由的边界”等议题,听起来深刻,实则每一句话都能在归序盟数据库中找到对应模板。
但他的伪装,败给了一个四岁女孩。
那女孩不识字,也不懂哲学,只是在他又一次宣讲“理性优于情感”时,忽然走到他面前,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轻声问:“你小时候哭过吗?”
男孩愣住。
他没有程序设定来应对这个问题。
他不知道该回答“否”以维持形象,还是该回答“是”以显得真实。
就在这一瞬间的迟疑中,他体内的人工信念链出现了裂痕。
当晚,他做了人生第一个梦。
梦见自己站在一口井边,井水清澈见底,映出的却不是他的脸,而是一个不停哭泣的小孩。
他想伸手去抱,可身体僵硬如铁。
醒来后,他撕碎了所有教材,在日记本上写下第一句真心话:
“我不想当完美的工具。”
然后,他逃跑了。
越来越多的“伪提问者”开始崩溃。他们本应是秩序的继承者,却被最原始的问题击穿防线。原来,真正的提问从来不是智力游戏,而是灵魂的痉挛,是心口突然涌上的酸楚,是明知得不到回应仍忍不住开口的冲动。
南极石碑依旧矗立,蓝光稳定旋转。
但科学家发现,它的高度正在极其缓慢地上升,每年约0。3毫米,方向垂直于地壳。地质学家惊恐地意识到:这不是建造,而是“生长”??它像一棵倒生的树,根须扎进地球深处,枝干指向宇宙。
与此同时,半人马座β星方向的飞船,舷窗闪烁频率再次改变。
从每分钟一次,变为每秒一次。
像心跳。
像倒计时。
空间站传来最新观测数据:地球夜晚的那只“眼睛”,轮廓更加清晰,瞳孔位置恰好对应中国西南部一处偏远山村??正是小女孩居住的地方。而每年冬至重现的“劫天运”极光文字,今年持续了整整十五分钟,最后一个字消散前,尾部拖出一道细微弧线,形似问号的钩端。
老学者们翻遍古籍,终于在一本失传的苗族口述史诗中找到线索:
“当天地闭眼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