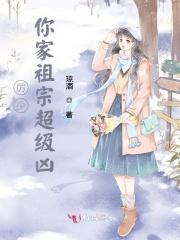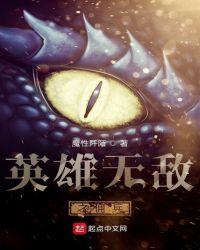笔趣阁>盖世神医 > 第3716章 开杀上(第4页)
第3716章 开杀上(第4页)
于是,他们在废墟上搭起简易棚屋,挂出一块木牌:
>**临时义诊:
>专治“不敢相信明天会好”。
>不收钱,只要一个承诺??
>好了之后,帮另一个人站起来。**
第一天,来了三个流浪汉,说自己“一辈子没用过”;
第二天,一对夫妻抱着自闭症孩子前来,母亲哭着说“我恨自己生不出正常的孩子”;
第三天,一位退役女兵拄拐而来,坦言自己每晚都被噩梦惊醒,却不敢告诉家人。
慧觉一一接待,听他们说完所有不堪、无助与悔恨。然后给他们一碗热汤,一颗蜜饯糖,再送一本手抄的小册子??那是老头留下的《共情医案手札》副本。
“看完它,如果你还想救人,就留下来。”他说。
十天后,第一批“毕业生”出现了。他们不再是垂头丧气的失败者,而是主动搀扶他人、倾听诉说的同伴。他们自称“半夏行者”,约定无论去往何方,都要在脚下扎根一处“安心角落”。
一个月后,这片废墟长出了第一株铃兰。
两年后,这里成为全国首个“情感生态试验区”,命名为“拾光新城”。街道以“理解”“包容”“等候”命名,学校不开设“排名榜”,医院设立“哭泣专用病房”,就连警察巡逻车都配备了“倾听员”。
而慧觉依旧每年春天回到渔村,在灯塔下教孩子们做蜜饯糖。
有一天,一个外国记者千里迢迢赶来,问他:“您认为这场变革的核心是什么?是制度?技术?还是思想启蒙?”
慧觉正在剥一颗橘子,闻言笑了笑,将一瓣放进嘴里,酸甜交织。
“都不是。”他说,“是信任。
是一个人敢在另一个人面前说‘我不行’,而对方不说‘你怎么这么弱’,反而说‘没关系,我陪你’。
就这么简单。”
记者愣住,继而落笔写下:
>“在这个崇拜胜利的时代,他教会人类另一种胜利??
>胜过孤独,胜过伪装,胜过以为必须完美才能被爱的恐惧。”
多年后,联合国档案馆保存了一份特殊影像资料:画面中,已是耄耋之年的慧觉坐在轮椅上,由小满推着穿过一片盛开的铃兰花田。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微风轻扬白发。
远处,无数年轻人身穿素白衣袍,手持烛火,缓缓走来。他们来自世界各地,职业各异,却有一个共同身份??“半夏行者”。
他们围成一圈,齐声诵读一段铭文:
>“我们曾以为强大就是永不跌倒,
>后来才知道,真正的盖世神功,
>是跌倒后敢说疼,
>是疼了还能笑,
>是笑着流泪,却依然愿意伸出手,
>对下一个颤抖的灵魂说:
>??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