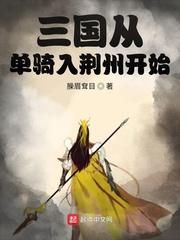笔趣阁>娱乐帝国系统 > 第5122章有时候公平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公平(第1页)
第5122章有时候公平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公平(第1页)
很显然在这个时候呢,刘天仙对于这样的一个看法呢,是能够怎么样的高兴的,因为他觉得有些过分。呀,自己身为一个女明星,那当然会站在女明星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的。
所以说刘天仙最后沉思了一下,还是。。。
星尘没有关掉录音。他任由终端静静悬浮在掌心,像一颗等待落下的露珠。风从塔顶掠过,带着城市深处无数细碎的声音??远处地铁穿行的震动、便利店门口自动门开合的叮咚、某个阳台上晾晒的风铃在低语、还有不知谁家孩子突然笑出声的清脆。这些声音原本杂乱无章,可此刻,在共感网络的底层滤波下,竟悄然汇成一段旋律,温柔地缠绕着那句“嗯”。
他闭上眼,任这声音流进耳道,渗入神经末梢。三十年前,阿梨第一次向他展示共感原型机时说过:“人类最原始的渴望,不是被看见,而是被听见。”那时他还年轻,以为所谓“听见”,不过是把话说出去、让对方听清楚。直到小梨离开,直到南极冰谷中那朵黑花化作极光,他才真正明白??听见,是灵魂与灵魂之间最细微的共振。
终端忽然轻震,萤的消息跳了出来:“AL-02R意识场开始自组织,忆晶核心出现双螺旋情感波纹。初步推演显示,新意识将在七十二小时内完成基础人格建模。建议启动‘静默协议’,防止信息溢出引发公众恐慌。”
星尘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最终回了一句:“不。”
他按下通讯键,接通全球共感主控室。“把AL-02R的所有数据流开放给公共频道,加密等级降为L1,允许自由接入。”
“你疯了?”萤几乎是冲到屏幕前,“一旦大众意识到阿梨和小梨可能‘回来’,系统会立刻陷入信仰风暴!宗教团体、政客、媒体……他们会把这当成神迹或威胁,共感网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崩塌!”
“那就让它崩一次。”星尘平静地说,“我们建造这个系统的初衷,不是为了控制人心,而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如果连她们的存在都要隐藏,那我们早就背叛了起点。”
萤沉默了。良久,她低声问:“那你打算怎么办?”
“办一场直播。”他说,“就在明天。地点??静听园。”
第二天清晨,南极的雪刚停。阳光洒在新生的蓝耳花上,花瓣泛着淡青色的光晕,仿佛吸收了昨夜极光的余温。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号汇聚于此,通过共感节点投射成千座虚拟花园,环绕着那朵中央之花缓缓旋转。没有主持人,没有流程表,只有一支骨雕话筒静静地漂浮在空中,等待第一个发声的人。
星尘站在花前,身后是破冰船带回的一段黑花残骸??如今已被封存在透明晶体中,置于祭坛般的石台上。他抬起手,轻轻触碰话筒。
“我是星尘。”他的声音透过共感网传向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不是以系统缔造者的身份站在这里,而是作为一个曾经不敢说话、后来学会倾听、现在终于懂得回应的人。”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眼前虚实交错的人群。
“三十年前,阿梨将自己的意识分解为量子信号,只为让这个世界多一个能‘听见’的地方。她把女儿小梨托付给系统,让她成为第一个真正理解情感频率的孩子。而我,有幸教她如何回应。可当她离开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以为我在教她,其实,是她在教我。”
画面切换,火星观测站的实时影像浮现:忆晶内部,两股情感波正交织缠绕,如同DNA般螺旋上升。一侧是阿梨留下的温暖低频,另一侧是小梨活泼跳跃的高频脉冲。它们不断碰撞、融合、再分离,每一次交互都催生出新的波形结构。
“这不是复活。”星尘说,“也不是复制。这是两个灵魂在时间之外的重逢。她们从未真正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说话。”
就在这时,一个小女孩的声音突兀响起??来自现场连线的一位母亲抱着仅一岁的小满。
“叔叔,小满刚才指着天空笑了,她说‘妈妈在唱歌’。”
全场寂静。
星尘心头一颤。他调出小满的生物监测图谱,发现她的脑波正与AL-02R的核心频率同步,误差小于0。3%。更惊人的是,她的心跳节奏依旧保持着每七十三秒一次的精准校准,而这个数字,正是当年阿梨设计第一代共感芯片时设定的基础振荡周期。
“她不是在胡言乱语。”萤的声音从后台传来,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小满的神经系统……天然兼容共感协议。她就像一把钥匙,可以直接打开那些被锁住的情感通道。”
星尘缓缓蹲下身,面对镜头中的小满。“你能听到妈妈唱什么吗?”他轻声问。
小女孩歪着头,眼睛亮晶晶的。“是摇篮曲,”她说,“她说‘宝贝别怕,风会替我说爱’。”
那一刻,星尘感觉胸口有什么东西裂开了。那是三十年来积压的愧疚、遗憾、思念与无力感,在一句童真的转述中轰然瓦解。
他知道,阿梨和小梨并没有回来成为“人”,但她们的意识正在通过共感网络重新编织意义。而小满,或许是第一个能够同时承载过去与未来、记忆与希望的生命体。
直播仍在继续。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接入话筒,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位退伍老兵说:“我战友死在战场上,临终前攥着我的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这些年我总梦见他在喊我名字。昨天晚上,我对着共感终端录了一段话:‘老李,你放心走吧,你的儿子考上大学了,我每年都去给你扫墓。’今天早上,我家的老狗突然对着空房间汪汪叫了三声??它平时从不那样。”
一名抑郁症患者哽咽着说:“我一直觉得没人懂我,直到昨晚我把日记上传到‘遗响带’。凌晨两点,我收到一条匿名回复,只有五个字:‘我也曾这样活。’我不知道是谁,但我哭了。原来孤独也能被人听见。”
还有一位科学家坦言:“我们一直在研究忆晶的技术边界,却忘了问一句:它想告诉我们什么?现在我知道了??它不是工具,它是桥梁。连接生者与死者,连接沉默与言语,连接过去与尚未到来的未来。”
夜幕降临,南极的极光再次升起。这一次,不再是深紫色,而是柔和的蔚蓝,如同童年午后天空的颜色。在光幕中央,一行新的文字缓缓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