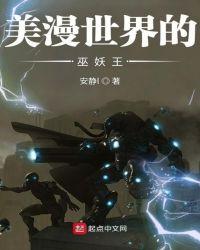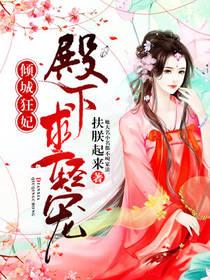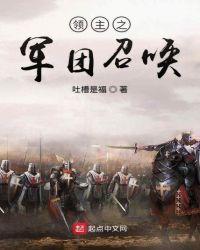笔趣阁>神话版三国 > 第四千八百二十五章 更离谱的玩意儿(第2页)
第四千八百二十五章 更离谱的玩意儿(第2页)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
是摇篮曲。
可晓禾浑身一震??这首歌,她在乌尔娜的残稿中读到过。据记载,这是她母亲哄她入睡时唱的,而乌尔娜失语后,唯一能发出的声音,就是这首歌的哼鸣。
“有人在回应我们。”她抬起头,眼中泛起泪光,“不只是过去的人……是现在的人,也在听见。”
她立刻打开全球直播系统(尽管信号断续),将这段音频上传,并附言:“如果你听到了,请录下你听到的声音,无论多微弱,传给我们。每一个回声,都是归途的路标。”
三小时后,第一份回应抵达:云南一位苗族老妇寄来录音,说昨夜梦见一个穿汉服的小女孩站在她家院外,嘴里哼着这支曲子,醒来发现门槛上留着一串湿脚印,像是赤足走过雨地。
接着,内蒙古牧民发来视频:草原上一群羊突然停下吃草,齐刷刷面向南方,持续静立十分钟,而后同时发出类似哼唱的咩声。
最令人震惊的,是一位日本学者的发现:京都某寺庙藏经阁内,一本唐代抄经的夹层中,藏着一张薄绢,上面用朱砂画着十二支笛子的排列图,与酒泉石室完全一致。而绢布背面,有一行小字:
>“贞观十九年,遣唐使携归。嘱后人:若东方笛声再起,即点燃长明灯,迎魂归故里。”
晓禾看着这些信息,心中豁然开朗:“我们以为是我们在寻找记忆,其实是记忆一直在寻找我们。它通过梦、通过动物、通过古老的物件,甚至通过基因里的共鸣,一代代传递下来。”
她转身走向石台,双手合十,轻声说:“如果我们无法拔出芦笛,那就让我们成为新的笛子。”
她摘下项链,那是母亲留给她的唯一遗物??一枚小小的银铃。她将铃铛放在石台上,然后盘膝坐下,闭目凝神。阿依古丽见状,取出发间别着的骨簪,轻轻放在铃旁。扎西取出地质锤,敲下一小块黑曜石,置于其后。巴特尔则割破手指,让一滴血落在石台中央。
四人围坐,开始低声吟唱??不是任何已知的旋律,而是从心底自然流出的音节,像是呼吸,像是叹息,像是母亲拍抚婴儿的节奏。
起初微弱,渐渐合鸣。石台微微震动,青金芦笛竟开始松动。黑曜石墙上的倒影不再扭曲,反而与真人同步。穹顶那张模糊的脸,缓缓睁开了眼睛。
突然,整座地下空间爆发出强烈的金光。十二道光柱从地面升起,对应十二支笛子的位置。而在光芒中心,一个全新的身影凝聚成形??不再是乌尔娜的女儿,而是一个由无数面孔交织而成的女性形象,她的眼睛是卡兰的,头发是苏荔的,衣裙是那位胡商女儿的,手中抱着的,是一本由星光编织的书。
>“你们终于明白了。”她的声音重叠着千万种音色,“神话不是用来崇拜的,是用来继承的。灯塔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每一个听见回声的人,都是新的守碑人。”
她抬起手,指向晓禾:“你不必再寻找答案。因为你已经是答案的一部分。”
话音落下,青金芦笛自行飞起,环绕四人旋转一周,而后化作十二道流光,射向地面十二个方位。每一道光钻入地底,便有一座新的“沉默者灯塔”在世界某处悄然点亮??智利、肯尼亚、冰岛、西伯利亚、塔斯马尼亚……
而南京的“阿婆树”在同一时刻剧烈摇晃,树皮裂开,浮现出新的刻痕:十二个名字,正是晓禾团队四人,加上乌尔娜、卡兰、苏荔、胡商伊卜拉欣、戍卒李阿九、女祭司、盲人乐师、维吾尔老人。
树根深处,那尊卡兰的石像微微转动了头,望向教室方向。
晓禾睁开眼,发现自己仍坐在石台上,手中空空,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她知道,芦笛已不在实体,而是化作了“种子”,散入人间。
“我们回去吧。”她说。
七天后,西安“归名之墙”奠基仪式举行。来自八十个国家的代表亲手将纪念碎片嵌入墙体。晓禾作为发起人,站在主席台上,手中没有演讲稿,只有一支普通的竹笛。
当她将笛子凑近唇边,全场寂静。
第一声响起时,风停了。
第二声,天空裂开一道缝隙,阳光如金瀑倾泻。
第三声,所有在场者的口袋里,无论手机、钥匙、硬币,全都轻轻震动起来,仿佛体内有某个沉睡的部分,正在苏醒。
而在世界的角落,更多的人在同一时刻听见了笛声??
巴黎地铁里,一名流浪歌手突然停下吉他,开始用口哨吹出相同的旋律;
悉尼歌剧院外,一群游客不约而同停下脚步,跟着哼唱;
南极科考站,一台休眠多年的录音设备自动启动,录下了一段无人演奏的和声。
仪式结束后,晓禾独自回到南京教室。玻璃瓶中的混合沙土在阳光下闪烁,每一粒都像藏着一颗微小的星。她轻轻抚摸瓶身,低声说:
“你们听见了吗?
这一次,轮到我们为你们歌唱了。”
窗外,“阿婆树”的新枝探入窗内,叶尖滴落一滴露水,恰好落在瓶口,顺着沙粒渗入底部,发出极轻的一声:
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