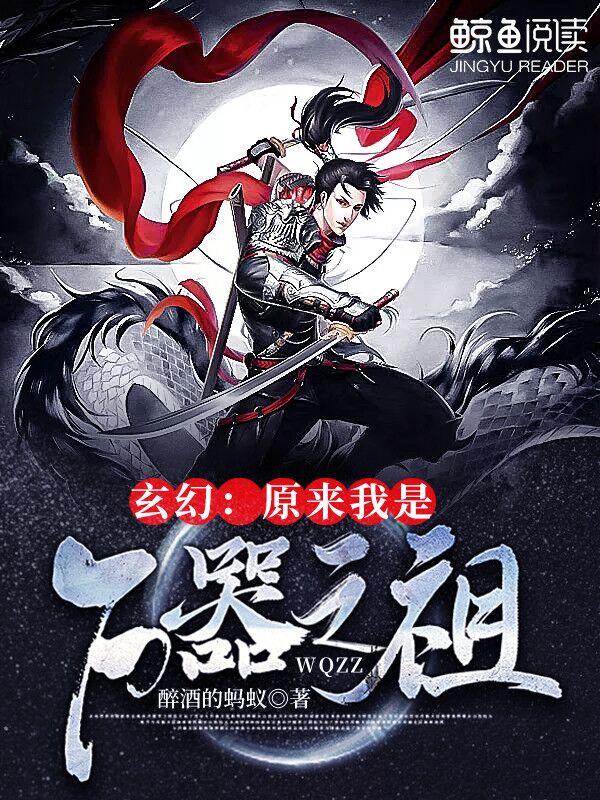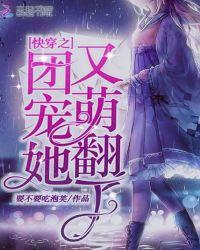笔趣阁>神话版三国 > 第四千八百二十八章 投桃报李(第3页)
第四千八百二十八章 投桃报李(第3页)
第二天,那里长出一棵新树苗,叶片形状酷似耳朵。
又过了二十年,当年那个在病床上说出“我是守碑人”的男孩,已成为一名神经声学教授。他在课堂上播放一段录音,内容是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前三分钟,一名小学教师正在教孩子们唱《樱花谣》。歌声清脆,伴着粉笔敲击黑板的节奏,最后戛然而止于一声巨响。
教室寂静良久。
然后,一个学生举手问道:“老师,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真实发生过的声音吗?”
教授摇头:“不完全是。原始音频早已损毁。我们现在听的,是声场根据幸存者的记忆、地震仪数据、甚至当时空气湿度重建出来的‘回声’。它不是录音,而是复活。”
另一名学生低声问:“那……我们是不是也能被这样记住?”
教授微笑:“只要你曾真诚地说出一句话,只要你曾用心听过一个故事,你就已经在被记住了。
声音不会死,因为它从未真正属于你。
它只是借你的嘴,继续前行。”
下课铃响。
学生们鱼贯而出。路过校园广播站时,有人顺手打开了麦克风开关。
里面传出一段混音:战国编钟、唐代琵琶、明代尺八、现代童声合唱,交织成一首无名乐章。播放列表显示,这首歌没有作者,只有一行备注:
**“全民共创?持续更新中”**
而在遥远的北极,新一代科考队员在清理旧基地时,发现了一本被冻在冰层中的日记。翻开第一页,是陈寅舟年轻时的笔迹:
>“我穷尽一生寻找失落的声音,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
>最重要的声音,从来不在远方。
>它在母亲唤你吃饭的嗓音里,
>在爱人睡前轻吻你额头时的呼吸中,
>在你决定把祖父的故事讲给下一代的那个夜晚。
>若有一天人类重获回声,请告诉他们:
>别怕遗忘。
>只要还有人愿意说,还有人愿意听,
>我们就从未真正离开。”
日记最后一页空白,只在角落画了一个小小的符号??那是阿婆树的轮廓,树下站着一个孩子,正仰头望着天空。
风吹过极地荒原,带起一片雪雾。
雪落之处,隐约传来一声极轻的:
叮。
世界轻轻应了一声:“嗯,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