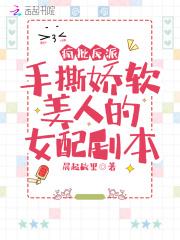笔趣阁>长夜君主 > 第九十章 剑大人传剑 二合一(第1页)
第九十章 剑大人传剑 二合一(第1页)
方彻挑挑眉,坏笑道:“我现在就让你成仙!”
夜梦顿时面红过耳,翻个白眼:“死相!”
“桀桀桀……”
方彻发出魔头的狞笑:“小娘子……”
事后。
夜梦很难得的没有睡过去,而。。。
山风拂过南疆祖林的旧址,如今已是一片葱茏。守心书院的钟声每日清晨响起,不为召唤信徒,只为提醒世人:天亮了,该醒来了。那口铜钟由九境百姓共同献铜铸造,无铭文,无图腾,只在内壁刻着一行小字:“光不属我,光在我行。”
承愿逝去百年之后,书院依旧如常运转。弟子们不再追求通天彻地的神通,也不再苦修古卷秘法。他们教孩童识字、为农人讲理、替孤老疗疾。有人问:“你们所传何道?”答曰:“不过教人记得自己曾被谁温暖过。”
这一日,春寒未尽,细雨如丝。书院外的小路上走来一位少年,约莫十五六岁年纪,衣衫虽旧却整洁,肩头背着一只破布囊,脚上草鞋磨得只剩半双。他步履沉稳,眼中不见疲惫,唯有坚定。门前值守的年轻学徒见他走近,正欲开口询问,少年却先一步拱手行礼,声音清朗:
“我从北境来,走了四十九天。听闻此地可学‘如何点亮一盏灯’,特来求教。”
学徒一怔。这话不是寻常问法。百年前,林小凡初入祖林时,也曾这般问过。
他不敢怠慢,引少年入院。穿过白墙长廊,两旁种满蓝雪花,雨珠滚落花瓣,宛如泪滴。少年走得极慢,似在用心记住每一步脚印的位置。
主殿空阔,中央石墙静立,映出窗外雨色朦胧。一位年长讲师正在讲授《愿力学说》,见少年到来,停了下来。
“你可知为何我们要在这里建一座没有神像的书院?”讲师问道。
少年摇头:“不知。但我想,若真有神明,?定不愿被人供奉,而更愿看见人间灯火长明。”
众人默然。片刻后,讲师点头,请他在角落席地而坐。
课程继续。今日所讲,是“归源之后的世界”。讲师说:“从前,光明集中于一人之身,林小凡背负九境希望行走十年,终将愿力散归众生。自此,不再有唯一的持灯者,却有了无数微光。我们不必成英雄,只需在别人冷时递一件衣,在他人暗时燃一豆火。”
少年静静听着,手指轻轻摩挲布囊边缘。待课毕,他起身走到石墙前,凝视良久。
“你能看见什么?”一名女弟子好奇问。
少年低声答:“我看见一个女人在雪地里生孩子,接生婆冻僵了手,可她仍用牙齿咬断脐带;我看见一群灾民围坐在废墟中分食最后一碗粥,每人只喝一口;我还看见……一个男人跪在坟前烧信,纸上写满了‘对不起’。”
女子动容:“这墙从不说谎。它照见的是你心里最深的共鸣。”
当晚,少年独坐院中,打开布囊,取出一盏小小的油灯。灯身斑驳,灯芯枯萎,显然多年未曾点燃。他从怀中摸出一小块蜡脂,小心翼翼涂抹于芯上,又划燃火石。
三试,未成。
第四次,火星跳跃,终于引燃。火焰微弱,在风雨中摇曳,仿佛随时会灭。少年却不急不躁,脱下外衣撑起一角,为灯火挡风。
这一幕恰被巡夜的老执事瞧见。他驻足许久,最终轻叹一声,转身离去,回房取来一本泛黄册子??那是《守心录》的抄本残卷,原本早已化作光柱升天,如今世上仅存数份手抄流传。
次日清晨,老执事将书递给少年:“你想学点灯,先要学会护灯。昨夜你做得很好。这书送你,不必谢我,只望你将来也能这样传给别人。”
少年双手接过,深深一拜。
七日后,少年开始随众听讲、劳作、扫院、煮饭。他话不多,但做事极认真。孩子们喜欢围着他玩,因他总会默默帮他们修好断掉的风筝线,或是把滑落山坡的课本追回来。
一个月后,书院迎来一年一度的“思灯祭”。月圆之夜,千盏素纸灯笼悬于枝头,随风轻晃,如同星河倒垂。众人齐聚广场,静默片刻后,齐声诵读《长夜纪事》最后一章。声音低缓而有力,穿透雨雾,传向远方村落。
诵毕,按例由一名新弟子上前点亮主灯台上的青铜古灯??那并非神器,只是象征。以往皆由讲师指定人选,今年却无人提名。
就在众人迟疑之际,少年走上高台。他手中捧着那盏旧油灯,轻轻放在青铜灯座旁,然后俯身吹熄了自己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