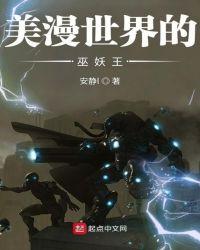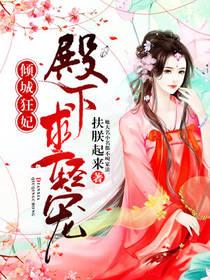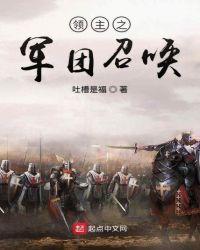笔趣阁>青葫剑仙 > 第两千五百四十四章 逆天行(第2页)
第两千五百四十四章 逆天行(第2页)
青年握紧玉佩,心中豁然开朗:原来记忆之路,从来不止一人独行。江湖之远,庙堂之高,市井之杂,边陲之僻,皆有默默执笔者。他们或许不知“续行人”之名,却早已践行其道。
他将日记本取出,撕下一页空白纸,提笔写下《忆行商规十条》,交予首领:“不必拜神,不用盟誓。只愿诸位送货之时,多问一句‘这信,是要给谁看的?’若对方已逝,请念一遍再烧;若尚在人间,请亲手交到手中。”
商队首领郑重收下,当场焚香立誓。
自此,“忆行商帮”声名远播。他们的驼铃不再只为财货而响,更为亡魂传音、为生者寄情。有人笑他们愚,说“一封信值几文钱”,但他们回答:“可对那个人来说,就是一生。”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
又是一年清明,青年回到最初启程的那个村庄。石桥仍在,小路依旧,只是村口多了块新碑,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不是烈士名录,也不是族谱排行,而是村民们自发记录的“身边好人榜”:张婶冬日为流浪猫搭窝,李叔冒雨送迷路孩童回家,王老师三十年义务教村童识字……
他站在碑前久久不语。
一位白发老太太拄拐走近,眯眼打量他:“你……是不是几年前在这儿歇脚的先生?你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记住别人的好,世界就不会彻底变坏。’”
他微笑点头。
老太太忽然哽咽:“我儿子去年走了。临终前交代,要把他这些年帮人修房、挑水的事写上去。我说没人会看,他说:‘总会有人看的。’现在我知道了,你看过了。”
他轻轻抚摸碑文,指尖传来温热。他知道,这不是石头的温度,而是千万颗心共同点燃的火焰。
当晚,他宿于村中小学。教室墙上贴满学生作文,标题皆为《我最难忘的一件事》。一篇写道:“奶奶说爷爷死了很久,可昨天晚上,我梦见他回来了,穿着旧军装,对我笑。醒来后,我发现枕头湿了,好像他也哭了。”另一篇写道:“爸爸从来不讲故事,今天却突然说起他小时候挨饿的日子。他说,以前不敢讲,怕人笑话,但现在不怕了,因为老师说了,说出来就不怕忘了。”
他一页页读着,直到东方既白。
晨光中,他取出日记本,准备继续书写新的篇章。可当他翻开扉页,却发现原本清晰的“第千零一世续行人”字样正在缓缓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文字:
>“吾无所名,故能遍历众生。
>吾无所执,故能常驻初心。
>此身可朽,此志不灭。
>青葫落地处,即是归途。”
字迹浮现完毕,整本日记忽然化作点点青光,融入晨曦之中,消失不见。
他并不惊讶,只是抬头望天,见一轮朝阳喷薄而出,照亮山河万里。
他知道,日记从未真正存在过。它只是万千人心中那一念不肯遗忘的具象。当所有人都开始书写,执笔者便不再需要名字。
他起身走出校门,迎着阳光迈步前行。
腰间的草铃铛轻轻晃动,发出细微声响,仿佛回应着远方某个孩子的期盼。
前方,是一座尚未命名的小城。城门口聚集着一群年轻人,正忙着张贴一张告示:
>“招募‘记忆守护员’:
>不限出身,不论学问,
>只需一颗愿意倾听的心。
>报名地点:忆馆(原茶馆二楼)。”
他驻足片刻,微微一笑,然后缓步走进人群。
没有人认出他。
但当他在报名册上签下第一个字时,那只青葫芦悄然从天而降,悬于忆馆屋檐之下,滴下一滴清露,正好落在册页中央,晕开一圈如莲绽放的墨痕。
风起时,全国一百零八个忆馆同时亮起灯火。
北疆雪原上的“血书碑林”泛起柔光,仿佛有人在夜中朗读;
江南湖畔的忆灯亭里,油灯无风自明,映出层层叠叠的身影;
西域“忆文堂”的书信墙上,风声诵经般低回不息;
东海灯船节的海域,青光再度汇聚,形成巨大的“记得”二字,悬于海天之间。
而在昆仑山顶,忆源殿中的源井泛起涟漪,盲女伫立井边,嘴角浮现笑意。
她听见井底传来无数声音,齐声低语:
>“纵使天地忘我,我亦不忘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