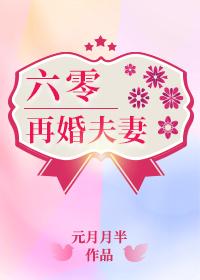笔趣阁>医路坦途 > 第九百章 栓法不同(第2页)
第九百章 栓法不同(第2页)
当晚,村委会召开家长会。十几盏马灯挂在墙上,映得人脸忽明忽暗。张凡没有放PPT,而是请古丽娜讲述她在南疆亲眼见过的一个故事:一名先天性白内障的女孩,手术后第一次看见母亲的脸,扑进怀里嚎啕大哭,“妈妈原来这么老啊,可你真好看。”
屋里有人开始抹泪。
接着,他展示了便携式OCT拍出的眼底图像??正常视网膜如星空般清晰,病变的则像被浓雾笼罩。“这不是诅咒。”他说,“这是身体在求救。就像牛生病了要治,孩子的眼睛也是。”
一位年长的牧民站起来,声音低沉:“你说得容易。我们祖辈都没看过这种机器,凭什么信你?”
张凡取下眼镜,指着自己鼻梁上的压痕:“我小时候也看不清黑板,差点辍学。是一个老师借我钱配了第一副眼镜。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有人愿意弯腰捡起一颗快熄灭的火星。”
会议室陷入长久沉默。最后,村长开口:“让我们试试。但你要答应我们,每一步都要告诉我们为什么。”
接下来的五天,张凡带领团队完成了全村儿童的全面筛查。共发现23例高度近视合并早期黄斑变性,8名儿童需尽快转诊。最难沟通的是一个叫库尔班的十岁男孩,右眼视力仅0。05,左眼因长期揉搓引发圆锥角膜,情况危急。其父坚决反对治疗,声称“眼睛变形是安拉的旨意”。
张凡第三次登门时,带上了艾尔肯教授的远程视频连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医生用维吾尔语耐心解释病情,并邀请库尔班的父亲参观乌鲁木齐一家已完成类似手术的孩子家庭。当视频里那个曾经几乎失明的女孩笑着背诵《古兰经》章节时,男人的手微微颤抖。
“我不是要改变信仰。”张凡轻声说,“我只是想让你的儿子也能这样读书。”
三天后,父子俩跟着医疗队下了山。临行前夜,母亲悄悄塞给张凡一袋晒干的玫瑰花:“这是我们家最好的东西,请您替我们照顾好他。”
返程途中,暴风雪突袭山路。车队被困七小时,食物耗尽,通讯中断。张凡蜷缩在车里,靠回忆支撑意志??阿?的笑容,泸水清晨的第一缕人造晨光,库尔班父亲终于松动的眼神……他忽然意识到,这条路永远不会轻松,但每一次突破文化的厚壁、跨越认知的鸿沟,都是在为“被忽视的生命”正名。
回到苍北医院时已是深冬。他顾不上休整,立即召集“烛瞳”项目组开会。闫晓玉带来了最新进展:系统已完成AI模型迭代,可通过面部微表情识别自动判断儿童是否存在视疲劳倾向,准确率达91。7%;同时,教育部同意将“视觉健康教育”纳入乡村教师培训必修课。
“下一步呢?”有人问。
张凡站在投影幕前,调出一张中国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已接入系统的学校。“我们要建一座‘流动的眼科方舱’。”他说,“改装成适合高原、荒漠、海岛等多种地形的模块化医疗单元,配备全自动筛查设备和卫星通讯模块,真正实现‘走到哪,诊到哪’。”
会议室一片寂静,随即爆发出掌声。
三个月后,首辆“萤火方舱”在青海果洛投入使用。它由退役救护车改造而成,顶部装有太阳能板,内部集成手持式眼底相机、智能验光仪与5G远程会诊终端。车内温度恒定,灯光模拟高原日照曲线,连座椅角度都经过人体工学优化,专为长途颠簸设计。
第一批受益者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夏令营营地。孩子们排着队走进方舱,好奇地盯着自动对焦的镜头。“像不像照相机?”张凡逗一个小女孩。
“像魔法盒子!”她咯咯笑。
检测结果显示,该营地42名儿童中有19人存在未矫正屈光不正,最高一名达-8。00D。所有数据实时上传至国家视觉健康档案平台,同步推送给属地疾控部门。三天内,定制眼镜通过邮政绿色通道寄达。
与此同时,阿依努尔传来好消息:决明子肽剂在塔县试点重启,配合民族文化宣讲团深入牧区,接受率回升至89%。库尔班术后视力恢复至0。8,写来一封信,末尾画了一颗太阳,写着:“医生叔叔,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像它了。”
春天到来时,张凡再次收到教育部通知:基于“萤火计划”系列成果,《乡村学校健康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修订草案通过审议,明确规定每所学校必须配备基础视觉筛查工具包及防蓝光护眼照明系统;财政专项拨款每年不低于五亿元,连续实施五年。
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一行字:“制度的光照进现实,比任何技术都更有力量。”
某个深夜加班归来,他路过医院儿科病房。透过玻璃,看见一个小女孩戴着卡通框架眼镜,正趴在床头读绘本。她抬起头,冲他甜甜一笑。那一瞬,他仿佛看见阿?、库尔班、泸水的孩子们,全都站在那笑容之后。
手机响了,是闫晓玉发来的消息:“新版本‘烛瞳’上线了情感反馈模块。现在不仅能预警疾病,还能感知希望。”
他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回复道:“那就让它继续跑下去吧。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没看清这个世界,我们的路就没有尽头。”
风起了,掀动桌角的日历。日期停留在四月七日,世界卫生日。远处,第一缕阳光正爬上医院楼顶的国旗杆,缓缓展开一抹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