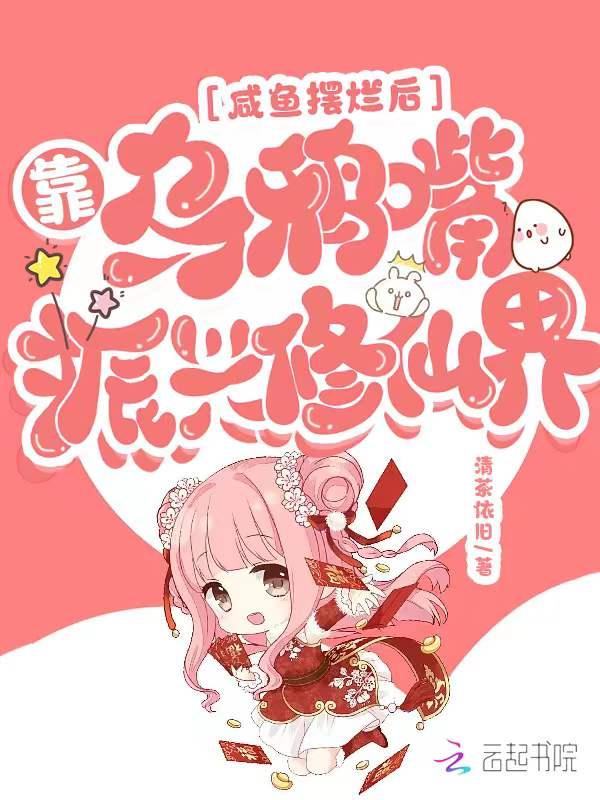笔趣阁>国公府真千金回来了! > 整顿官场一更(第3页)
整顿官场一更(第3页)
本来审案的时候岑暨是准备给燕宁安排一个专座的,就像先前在澧县旁听那样,但今日出庭的人有些多,燕宁也不想喧宾夺主,就拒绝了岑暨这一好意,主动要求退居幕后,只躲在屏风后听热闹。
显然,事实证明,确实是挺热闹的。
见燕宁露面,岑暨脸上尚存的冷然之色瞬间如潮水般退去,只见他轻咳了一声:“你听见了没,那张全说我是个好官。”
“听见了。”燕宁点头。
“那你怎么看?”岑暨似是不经意问。
见岑暨面上一本正经,如一座高冷不容玷污的雪山,仿佛只是随口一问,但眼角余光却时不时掠过她,显然在无声期待下文,燕宁差点失笑,这表情简直不要太好懂,只差没把“求夸夸”这几个字写脸上了。
“嗯”
在岑暨隐含期待目光中,燕宁故作迟疑,眼看他眸中光亮渐黯,燕宁倏地一展眉:“怎么不算呢?”
岑暨心中才刚升起的一丝失落瞬间消散地无影无踪,就连故意绷着的脸都随之软化,见燕宁笑脸盈盈模样,他嘴角不自觉扬起微小弧度,目光灼灼:“你真这么觉得?”
凭心而论,燕宁确实觉得岑暨在这方面做的还不错,就算身上大大小小毛病不少,但就冲他方才怼王少卿那番话也足以证明至少三观没歪。
越是身居高位的人,就越难对人命产生敬畏之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具体从王少卿说乞儿之命比不上王天昱的就能窥出一二。
“嗯。”
燕宁觉得岑暨这样子像极了得了老师夸张的小学生,见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燕宁毫不吝啬表示赞同之余,还不忘给予勉励之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再接再厉。”
岑暨:“?”
“对了,张全的案子你打算怎么判?”
王少卿夫妻俩晕的太快,堂上都乱成了一锅粥,所以张全的罪名并未来得及当堂宣判。
对于燕宁的问题,岑暨沉吟了一下,不答反问:“你想怎么判?”
燕宁:“”
“这是我怎么想就能怎么判的吗?”
没想到岑暨居然还搁这儿踢皮球,燕宁一噎。
“可以作为参考,所以”
岑暨看着她:“你怎么想?”
“我什么都没想。”
见岑暨当真作出一副侧耳聆听模样,燕宁忍不住锤了他一拳:“刚还夸你来着,这会儿就又飘了,你怎么判案关我一仵作什么事儿,别整的跟一昏庸君王似的。”
其实从私心里说,燕宁对张全是有一份恻隐之心的,哪怕他背了两条人命,但同样燕宁也清楚,就算是情理与法理兼具那也是有限度的,刑狱断案最忌讳的就是感情用事。
张全杀人出发点虽说是为弟弟报仇,但到底是杀了人,手段还颇为残忍,杀的又是官宦子弟,各方面施压,张全怕是难逃一死。
岑暨再次挨揍,这回却未生出忿恼,看着融融烛火下燕宁秀美面庞,他眸光微闪,心中迟疑的想,若他是昏庸君王,那她岂不就是
“我朝律法,凡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但具体视情况而定,张全杀人是为报仇,有王天昱与陈奔害死乞儿在先,也算事出有因,且张全是主动投案,律例有定,‘既道称道尽输其情,不敢隐匿,罪虽大,时乃不可杀’”
岑暨缓声:“杖二十,流两千里。”
大庆刑罚从轻到重一般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种,死刑无疑是最重的一档,而张全杀了两人却只被岑暨判了流刑。
虽说罚的照样不轻,但最起码比直接杀头要强,正所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如果遇到大赦还能提前释。
燕宁没想到岑暨会不判斩,当然了,这其中张全主动投案的行为起了很大作用,本来是破罐子破摔,却没曾想反给自己谋了一线生机,也是张全命不该绝。
不过
“你可真是头铁啊!”燕宁忍不住再次朝岑暨竖起了大拇指。
要知道王家可是叫嚣着要千刀万剐的,结果他倒好,连死刑都没给判。
燕宁这句话说的没头没尾,岑暨却奇迹般的听懂了,只见他轻哼了一声:“本官秉公断案,还轮不到外人指手画脚随意置咄,若有异议,大不了去御前公决。”
“还有京兆府那帮饭桶。”
岑暨目露阴鸷:“一个个敷衍塞责素餐尸位,有人报案却还敢置之不理拒于门外,看来真是安逸日子过太久了,都忘了自己该干什么,是时候让他们长长记性了。”
看着摆明了不准备就此善罢甘休的岑暨,燕宁:“”
好么,这是要开始整顿官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