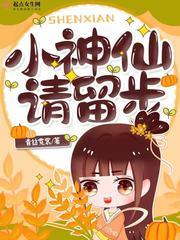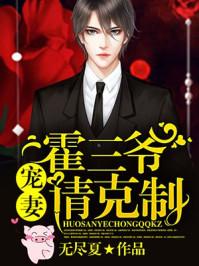笔趣阁>傲世潜龙 > 第3216章 怀疑身份(第2页)
第3216章 怀疑身份(第2页)
原来共感不仅能净化情绪,还能唤醒被遗忘的真相。
接下来七日,类似场景接连上演。
一位中年女性坦白自己曾在丈夫车祸身亡后,对着瘫痪婆婆恶语相向,只因无法接受“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一名医生承认,在疫情最严重时,他曾私自调换重症床位顺序,只为保住一位有权势病人的性命;甚至还有一位老人,颤抖着说出自己年轻时参与过一场集体暴力事件,几十年来每夜都被受害者的眼神惊醒。
每一次倾诉,铜锅都会以不同方式回应:有时浮现旧日影像,有时让讲述者看到对方视角的经历,有时则只是静静地吸收那份沉重,将其转化为星空中一抹新光。
人们开始称这种状态为“镜映”。
不是评判,不是宽恕,也不是治愈,而是让每一个灵魂都能在另一个灵魂中照见自己原本的模样。
然而,变化也在悄然滋生。
某夜,一名陌生男子闯入“舟记”,身穿黑色风衣,眼神冷峻。他不坐,不语,只盯着墙上沈知遥的画像看了整整一个小时,然后突然冷笑一声:“你们所谓的共感,不过是情感麻醉剂罢了。”
苏晚迎上前:“你有话想说?”
“我说了你会听吗?”他反问,“还是等我哭出来,你们就又拿那口锅当圣物,把我打个标签??‘需要疗愈’‘内心创伤’‘渴望被理解’?”
店内气氛顿时紧绷。
陈烈悄悄靠近监控面板,发现此人脑电波频率竟与深海石屋中的某座高度吻合??正是那位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心理咨询师赵慕云,主张“理性克制高于情感宣泄”的代表人物。他的信念曾被视为共感体系的对立面,但在最新一轮数据分析中,其意识片段显示出强烈的回归意愿。
苏晚却不动怒,只是搬来一把椅子,放在男子面前,轻声说:“你说得对。我们确实容易把痛苦浪漫化,把眼泪当成救赎的象征。可如果你觉得这是表演,那你告诉我??什么才是真实的倾听?”
男子怔住。
良久,他缓缓坐下,声音低沉下来:“真实……是即使我不哭,你也愿意信我;是我骂人、发疯、沉默,你依然不急着给我贴药膏;是我告诉你‘我不想变好’,你也能点点头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坏一会儿’。”
他说完,铜锅忽然发出一声闷响,锅盖轻微跳动,却没有蒸汽溢出。紧接着,锅底第八道刻痕亮了起来,光芒流转,竟与男子手腕上一道旧疤的脉络完全重合。
苏晚心头一震。
她终于懂了。
这第八座石屋,不是补充,而是**平衡**。
前七位执灯人分别代表七种基本情感原型,而第八位,则象征着**怀疑者**、**质疑者**、**反对者**??那个始终站在光之外,提醒所有人“别忘了黑暗也值得尊重”的存在。
而这名男子,正是赵慕云意识选中的容器。
从那天起,“舟记”开启新规则:不再设门槛,不限身份,不论言辞是否刺耳。你可以赞美,也可以诅咒;可以忏悔,也可以挑衅;可以说我爱你,也可以说去死吧。只要你是真心,锅便接纳。
渐渐地,这里不再是疗愈圣地,而成了人类心灵的**试验场**。
有人在这里宣布退出共感网络,说自己宁愿孤独也不愿被窥探;有人公开支持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引发激烈辩论;甚至有个少年写下长达万字的日记,控诉父母以“爱”之名实施的精神控制,最后烧毁全文,只留下一句:“我不是要你们同情我,我只是不想再假装幸福。”
每一次风暴过后,铜锅都会经历短暂停滞,仿佛在消化这些复杂信息。但最终,总有新的星光升起,连接成前所未有的图案。
心理学家们震惊地发现,全球范围内的自杀率连续三个月下降,抑郁指数趋稳,人际信任度回升。更令人费解的是,许多从未接触过“舟记”的普通人也开始自发组织“倾听聚会”??在公园长椅、地铁车厢、学校天台,两人一组,轮流讲述心底最深的秘密,不打断,不评价,只说一句:“我听见了。”
媒体称之为“静默革命”。
而在南太平洋海底,第八座石屋开始发生变化。水晶墙体逐渐变得半透明,内部木桌延伸出七把椅子,象征八位执灯人终将齐聚。笔记本扉页新增一行字迹,非林舟手书,却笔力苍劲:
>“共感非顺流,亦非逆流,
>而是允许百川奔涌,各归其道。”
苏晚读到这句话那天,正值春分。
她独自登上云音谷雷达站,启动尘封已久的接收系统。信号自动校准,锁定南极冰层下方一处隐秘节点。画面缓缓浮现:一座冰窟之中,摆放着一台老式录音机,磁带仍在转动。按下播放键,传出一段断续女声:
“这里是周文素……第102,8通来电记录……来电者是一名高中生,他说班上有同学跳楼了,可没人敢提她的名字,因为‘她成绩不好,性格孤僻,死了也是活该’……我想告诉他,每个人都有权利被记住……哪怕只是存在过……”
录音戛然而止。
苏晚关掉机器,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