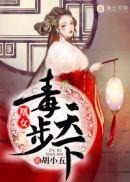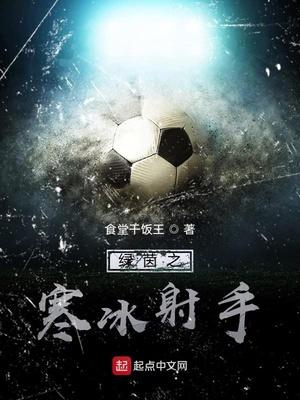笔趣阁>我有十万亿舔狗金 > 1690 乡巴佬(第1页)
1690 乡巴佬(第1页)
“多少钱?三万?”
得知价格,还觉得这条皮带还挺好看的兰母顿时瞪大了眼。
三万块。
一条腰带。
别说农村人,就算城里人也多半没法接受。
她专程拎来一年才结果的橘子,才多少。。。
山道蜿蜒,车轮碾过碎石发出细碎的声响。江辰坐在副驾驶,手里攥着那条蓝围巾,指尖一遍遍摩挲着边缘磨损的线头。林晓雯在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轻轻放了一张CD进去。钢琴声缓缓流淌出来,是肖邦的《夜曲》??母亲生前最爱的一首。
车子驶进下一个县城时,天已微亮。他们要在城郊的实验小学开启“微光计划”的第三站。这所学校比临沧村条件好些,有塑胶跑道和多媒体教室,但校长接待他们时神情复杂:“上级刚发了通知,说最近有学生模仿网络言论写‘遗书体’日记,要求我们严查心理异常学生。”
江辰把背包放在会议室桌上,平静地问:“然后呢?你们怎么处理?”
“能怎么办?”校长苦笑,“请心理老师谈话,让家长带回家观察……可有些孩子回来就说更难受了,家里像审犯人一样盘问他们是不是真想死。”
林晓雯从画箱里取出几张打印好的画作,摆在桌面上。“这些是我们收集的真实作品,来自不同年龄的孩子。有没有可能,所谓的‘异常’,其实是他们在用唯一会的方式求救?”
校长盯着其中一幅:一个穿校服的女孩漂浮在黑色河流上,双手被无数红色丝线缠绕,连向岸边一个个模糊的人影。标题写着《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撑不住了》。
他喉结动了动,声音低下去:“我女儿去年休学三个月……她也是这样。”
江辰点头:“所以问题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在我们是否愿意听懂他们的语言。”
上午九点,第一堂课开始。阶梯教室坐满了五年级到初一的学生,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好奇。江辰没有直接讲课,而是打开投影,播放一段无声视频:镜头扫过空荡的卧室、翻倒的椅子、桌上未吃完的药片,最后停在一面贴满便利贴的墙。每张纸条都写着一句话:
>“你们说我命好,可我觉得活着像在还债。”
>“我考第二,我爸问我为什么不拿第一。”
>“妈妈哭的时候,我会假装看不见,因为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又让她失望。”
画面结束,全场寂静。
“这不是某个自杀未遂者的房间,”江辰开口,“这是全国两千三百七十六名青少年匿名投稿拼接而成的真实空间。他们不是疯子,也不是矫情,他们只是太久了没人肯认真听他们说话。”
有个女生举手,眼圈泛红:“老师,如果我说了,可是爸妈根本不信呢?他们说我现在吃穿不愁,有什么可难过的?”
“那你有没有试过换一种方式让他们看见?”江辰问。
她摇头。
“今天我们就来做这件事。”他转身写下今天的主题:**让你的秘密长出形状。**
孩子们领到素描纸后,林晓雯开始示范如何用色彩表达情绪。“愤怒不一定非得是红色,它可以是撕裂的线条,可以是压满整页的粗黑笔触;悲伤也不只是蓝色,它可能是灰蒙蒙的一片空白,也可能是一颗藏在角落的小糖纸??因为你记得还有人给过你一点甜。”
一个戴眼镜的男孩迟迟不动笔。江辰走过去轻声问:“你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该不该画。”他咬着嘴唇,“我想画我爸打我的样子……但我怕被人看到。”
“那就先画给自己看。”江辰递给他一支深灰色铅笔,“你可以只画他的影子,或者那只举起的手。甚至,你可以画一道门,把自己关在里面。”
男孩沉默良久,终于低头画了起来。他画得很慢,每一笔都像在承受重量。二十分钟后,纸上出现一间狭小的卫生间,门缝透出客厅的灯光,门外传来摔东西的声音。一个小人蜷缩在马桶盖上,手里紧紧抱着一本漫画书,封面上写着《超人不会哭》。
江辰在他旁边坐下:“你觉得超人真的不会哭吗?”
男孩摇头:“可大家都希望我像超人。”
“可你不是超人,你是个人。”江辰说,“而人本来就会疼,会怕,会想要躲起来。”
下课铃响时,那个男孩主动把画交给了江辰。“我能留个复印件吗?”他小声问,“我想……哪天偷偷夹在我爸枕头底下。”
江辰郑重地点头:“我相信他会读懂的。”
中午休息时间,江辰正在整理影像资料,手机震动。是茜茜的消息:
>“教育部正式批复‘静语十分钟’试点方案,首批覆盖五十所乡村学校。但他们提出一个条件:必须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防止‘负面情绪聚集引发群体效应’。”
江辰回道:
“告诉他们,真正的聚集不是传染悲伤,而是传递勇气。我们不需要评估数据是否‘安全’,我们需要的是允许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