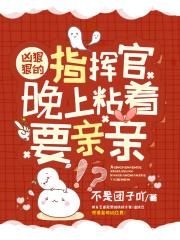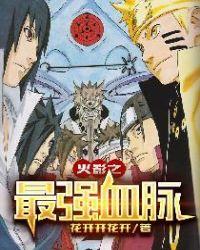笔趣阁>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 第683章浪打浪根本停不下来(第2页)
第683章浪打浪根本停不下来(第2页)
“正因为多数企业不愿做,才更需要有人带头。”陈着直视对方眼睛,“我不是号召所有企业都砸两亿搞培训,而是希望构建一种机制??让做好事的企业得到更多支持,让逃避责任的付出代价。比如税收优惠、政府采购倾斜、品牌信用加分。只要形成正向激励,自然会有越来越多企业加入。”
会议室陷入短暂沉默。
最终,常务副省长做了总结:“陈总的发言很有启发性。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公共服务的核心供给责任始终在政府。企业可以参与,但不能替代。下一步,可在珠三角试验区先行先试,边运行边完善制度设计。尤其要注意防范‘数据垄断’‘资本裹挟政策’的风险。”
散会后,周正德留下陈着聊了几句。
“你表现得很好。”老人轻声说,“没逞强,也没退缩。记住,体制最怕两种人:一种是蛮干的愣头青,一种是野心勃勃的挑战者。你要让他们觉得,你是第三种??共建者。”
陈着点头。
他知道,这场博弈远未结束。今天的会议虽未明确表态全面推广,但“试验区”三个字已意味着破冰。只要试点成功,后续推进便是水到渠成。
一周后,试验区正式启动仪式在东莞举行。省领导出席并揭牌,现场签约十家职业院校、五家行业协会及三十余家制造企业。媒体争相报道,“政企共建数字技能赋能平台”成为热词。
与此同时,陈着悄然推进另一项计划。
他在内部成立“未来教育实验室”,联合苗晓教授团队开发一套AI驱动的职业潜能测评系统。该系统可通过分析个体的学习行为、认知偏好、动手能力等维度,精准推荐最适合的职业技能培训路径。首批测试对象,正是全省登记在册的五千名辍学青少年。
一个月后,第一份报告出炉:其中有1872人具备智能设备维修潜力,943人适合进入工业机器人操作领域,另有三百余人展现出软件开发天赋。
陈着亲自带队走访其中二十个家庭。在一个湘西山村,他见到一个叫龙小雨的女孩。十六岁,父亲残疾,母亲外出打工多年未归。她每天走两小时山路去镇上中学旁听课程,自学Python编程,在B站上传了十几个教学视频,粉丝两万。
“我想考大学。”她怯生生地说,“但我连电脑都没有。”
陈着当场决定:将“未来教育实验室”升级为“追光计划”,每年资助一千名偏远地区青少年接受定制化技能培训,配备学习终端,安排导师一对一辅导。
消息传出,舆论再度沸腾。共青团中央官微转发报道,称其为“新时代的希望工程”。
而此时,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六月初,教育部突然发布征求意见稿:拟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纳入高考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作为高校录取参考依据之一。这意味着,一个农民工子女如果考取高级电工证,可能在高考中获得加分优势。
草案一经公布,立即引发激烈争论。城市middleclass家长群体强烈反对,认为这会削弱文化课成绩的公平性;而广大农村教师和基层教育工作者则拍手称快,直言“终于有人看见了沉默大多数的需求”。
关键时刻,陈着在《南方周末》发表署名文章:《我们欠小镇青年一条上升通道》。文中他写道:
>“当我们在讨论‘减负’时,很多孩子正打着三份零工攒学费;当我们强调‘素质教育’时,有些学校连美术老师都没有。如果我们一边呼吁教育公平,一边又拒绝承认非学术型才能的价值,那所谓的公平,不过是精致利己者的遮羞布。”
这篇文章迅速刷屏,三天阅读量突破千万。连一向保守的《光明日报》也刊发评论,呼吁社会各界理性看待多元化人才评价体系的探索。
七天后,教育部宣布:试点范围缩小至十个欠发达地市,暂不纳入全国统考加分项,但鼓励高校在自主招生中予以适当考量。
虽然妥协,却是突破。
陈着知道,自己已经触碰到中国社会最深层的神经??阶层流动。
这晚,他独自坐在办公室,翻看手机相册里那一张张学员的笑脸。忽然收到一条微信,是父亲发来的语音:
“儿子,村里广播说了,咱们县也被列入‘百万新工匠’计划覆盖范围。老张家的儿子报了你们的培训班,说以后要去深圳修机器人……你妈要是还在,一定为你骄傲。”
他闭上眼,泪水无声滑落。
第二天清晨,林小雨冲进办公室,手里挥舞着一份文件:“陈总!发改委批复了!‘数字经济就业创新试验区’二期扩容,新增五个城市!而且……”她喘了口气,“国务院参事室邀请你下周赴京,参加‘高质量发展与包容性增长’闭门研讨会!”
陈着望着窗外初升的太阳,轻轻吐出一口气。
他知道,这条路还很长。前方仍有无数阻力:既得利益者的反扑、舆论风向的突变、政策执行的变形……但他不再孤单。
因为已经有十万普通人,正借着他搭起的梯子,一步步爬出深渊。
而当足够多的人向上攀爬时,整个大地都会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