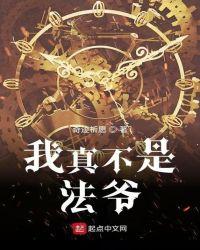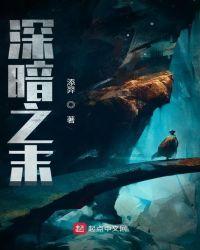笔趣阁>逍遥四公子 > 第1941章 王爷手书在此我看谁敢(第3页)
第1941章 王爷手书在此我看谁敢(第3页)
门帘掀开,寒气涌入。
进来的是个老人,白发如霜,面容清瘦,身上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脚穿草鞋,腰间系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铜铃。
他站在门口,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看着忙碌中的陈禾。
陈禾抬头,目光触及对方左耳那道熟悉的疤痕,手中银针“当啷”落地。
“您……”他喉头哽咽,“您回来了?”
老人微微一笑,声音清淡如风:“我没走,只是换了条路走。”
他缓步走入,从怀中取出一本册子,封面无字,纸张泛褐,显然是多年随身携带所致。他将册子放在桌上,轻轻推至陈禾面前。
翻开第一页,赫然是《守望录》的开篇之语:
>“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书;人间之痛,非一泪足以洗。然若有千人执笔,万人垂泪,则暗夜终有尽时。”
但接下来的内容却是全新的??记录着近三十年间散落在各地的“微光时刻”:某个山村女子自学医术救活难产妇人;某位狱卒偷偷放走无辜囚徒后自首伏法;甚至包括阿砚长大后创办义塾、苏萤培育盲童说书团队的全过程。
每一则故事,皆以极简之笔写就,却饱含温度。
陈禾颤抖着翻到最后一页,只见空白处有一行新添的小字:
>“此书至此,终章未成,亦无需成。因你们已在续写。”
>
>“铃响之处,即是归途。”
>
>??林隐绝笔
“绝笔?”陈禾猛地抬头,“您要走了?”
老人望向窗外,雪花静静飘落,覆盖了整座小镇。炊烟袅袅升起,孩童笑声隐约可闻。
“我不是要走。”他轻声道,“我是要融入。从此以后,我不再是林隐,我只是‘那个写过书的人’。而你们,才是故事本身。”
说完,他解下腰间铜铃,轻轻放在桌案上,转身离去。
陈禾追出门外,雪地上只留下两行足迹,延伸向镇外那棵历经风雨的老槐树。树下,铜铃随风轻晃,发出一声悠远回响。
多年后,归途镇建起一座纪念馆,名为“守望堂”。堂中最珍贵的展品,便是那只铜铃,以及林隐留下的最后一本手稿。每日清晨,都会有孩子轮流前来诵读一段《守望录》,声音清脆,穿透晨雾。
而在千里之外的西域雪山脚下,一间小小的茶棚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为过往旅人煮茶。有人问他姓名,他只笑而不答,偶尔提起陶壶时,袖口露出半截旧绸??正是当年铭心阁门楣上飘落的那一片红。
茶香氤氲中,他低声哼起一首古老的谣曲:
>“风起兮,铃响兮,
>谁在听,谁不忘?
>一念善,万山亮,
>归途不在远方,在心上。”
歌声落下,远方雪峰映着朝阳,金光万丈。
天地无言,唯有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