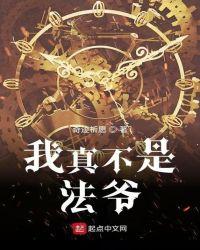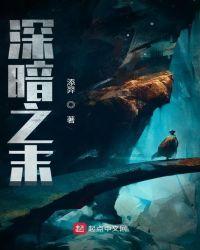笔趣阁>逍遥四公子 > 第1941章 王爷手书在此我看谁敢(第2页)
第1941章 王爷手书在此我看谁敢(第2页)
学生们纷纷跑回屋檐下,唯有阿砚仍守着那张湿了一角的信纸,慌忙用手遮挡。苏萤却轻轻按住他的肩:“别怕,雨水洗不去真心。”
话音未落,只见一名老仆模样的人匆匆从后院奔来,怀里紧抱一只木匣,高喊:“苏讲师!快看!井底冒光了!”
众人闻声聚拢。果然,透过浑浊雨水中翻涌的泥沙,井底竟透出幽幽蓝光,如同星火沉眠千年,终于苏醒。老仆颤抖着手打开木匣??里面是一盏古灯,灯身铜绿斑驳,灯芯早已熄灭,但灯座刻着一行小字:**燃于北境,照归人路**。
“这是……当年沈将军墓前的长明灯!”有人惊呼。
苏萤伸手抚过灯身,指尖忽然一颤。她虽看不见,却感知到了某种熟悉的气息??那是风沙、血迹、旧书页与铜铃共振后的余韵。她低声念道:“这不是灯,是信使。”
雨势渐歇,井中光芒也随之减弱,但在最后一瞬,水面倒影竟浮现出一行虚幻文字:
>“阿砚,我听见你了。”
>
>??林
全场寂静。连最调皮的孩子都屏住了呼吸。
苏萤仰起脸,任细雨沾湿鬓发。她知道,这不是幻觉,也不是传说。这是“守望”的律动??每当有人以真诚之心许下承诺,天地之间便会响起一次回应。或许无形,或许无声,但它确实存在,如心跳,如呼吸,如种子破土前那一声微不可察的裂响。
数日后,听铃书院迎来一位特殊访客。
那人一身粗布衣裳,背着药箱,左耳缺了一角,步履稳健,眼神温和。他是陈九的孙子,名叫陈禾,继承祖业做了游方郎中。他走遍南北,专治贫病,随身携带一本残破的《守望录》,扉页上写着祖父遗言:“手艺可以丢,骨头不能弯。”
他在书院外跪了整整一夜,只为求见苏萤一面。
次日清晨,苏萤亲自迎出。两人相对无言良久,最终陈禾从药箱夹层取出一封信,双手奉上。
信封泛黄,火漆已裂,收件人写着“林隐亲启”,邮戳模糊不清,只依稀辨得“西南孤峰”四字。
“这是我祖父临终前托人转交的。”陈禾声音低沉,“但等我赶到时,林先生已不知所踪。这些年,我带着它四处行医,总觉得……只要我还走在路上,他就还没走远。”
苏萤接过信,指尖轻抚封口,忽然察觉异样??信纸极薄,折叠方式奇特,像是盲文书写者的习惯。她小心拆开,展开内页,却发现纸上并无一字,唯有一幅用针尖刺出的凸点图案:一棵槐树,树下坐着一个孩子,手中握着铜铃。
她心头剧震。
这是只有她师父才懂的密语系统??当年那位拒认亲父母的盲女,正是用这种方式记录下林隐口述的每一个故事。而这幅图,分明是林隐少年时代在槐树下授学的情景。
“这封信……从未寄出。”她喃喃道,“它是林先生留给未来的钥匙。”
陈禾怔住:“您的意思是?”
“意思是,他还活着。”苏萤嘴角扬起一抹笑意,“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从未真正离开。他在等一个人,一个能把所有碎片拼成完整图景的人。”
“谁?”
“我们。”她将信纸轻轻贴在胸口,“每一个读过《守望录》、被其中一句话点亮过眼睛的人。我们就是他选择的续笔者。”
自此,听铃书院正式设立“守望日”,每年清明,师生齐聚井边,朗读一封未曾寄出的信,讲述一段无人知晓却真实发生的故事。有人讲西北沙漠中一位老驼夫,每夜点燃篝火,只为照亮迷途旅人;有人讲江南小镇上一对盲夫妇,靠说书维生,每月必抽出一日免费讲述《守望志》章节;还有人讲东海渔村的孩子们,自发组织“晨读队”,天未亮便聚在码头,一边补网一边背诵“为人之道”。
而在这些故事之外,总有一声铜铃轻响,或来自风中悬挂的旧铃,或来自某人心头蓦然闪过的良知觉醒。
时光流转,二十年光阴如江水流逝。
听铃书院已扩建成一座占地百亩的学府,四周阡陌纵横,稻浪起伏。昔日废城之地,如今百姓安居,孩童入学,商旅往来不绝。人们不再称其为“死城”,而是唤作“归途镇”。
这一日,春寒料峭,细雪初降。
镇东一间简陋医馆内,陈禾正为一名高烧患儿施针。门外积雪深厚,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缓慢却坚定,踩碎了雪地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