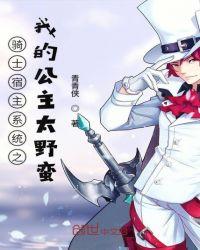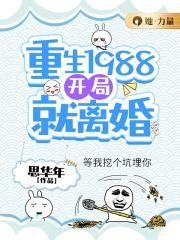笔趣阁>剑走偏锋的大明 > 第九百七十一章 定纲(第1页)
第九百七十一章 定纲(第1页)
而在于谦和陈循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忙碌时,潘筠正沉溺于数据书海中。
时机已到,她正从灵境中调出各种机器图和材料冶炼方法,拿笔一一抄录下来。
比如,建了铁路就需要火车,是用最基础的蒸汽系统,还是。。。
车队北上七日,行至黔东铜仁府境,天色骤变。乌云压顶如墨泼,山风穿谷似鬼啸。苏小荷掀开车帘,见前方山路已被泥石流截断,数十丈长的塌方堵住隘口,骡马惊嘶,寸步难行。押车的驿卒摇头叹道:“这等天气,怕是要困在此地三五日。”周玉娘冷笑一声:“三五日?京试在即,我们耽误得起吗?”话音未落,阿诗玛已跃下马车,从背囊中取出测绘罗盘与地形图,蹲身细察岩层裂痕。
“不是自然塌方。”她声音清亮如山泉击石,“你看这些断面,有斧凿痕迹,泥土翻动方向也不对??是人为炸开的。”众人愕然。苏小荷心头一凛,想起临行前夜,书院暗哨回报:近来有数批黑衣人沿滇黔古道北上,形迹诡秘,腰佩无铭铁牌。她凝视地图上那条蜿蜒红线,忽觉脊背发凉??这条路,正是“千里传灯”主脉之一,三年来已有百余所夜校依此线建立。
当夜宿于村庙,四人围坐油灯下议事。周玉娘拍案而起:“分明有人要断我们的路!若非阿诗玛眼利,明日便要葬身山腹!”苏小荷却沉吟不语,只将手中《公民手册》翻开,指着其中一页批注:“老师曾言,‘阻力越大,说明走得越近’。”她抬眼望向同伴,“他们怕的不是我们赴考,而是怕我们把实学的火种带到京城。”
次日凌晨,村民自发组织百人清障队,手持锄镐撬石搬木。一位老猎户指点隐秘小径:“翻过鹰嘴崖,可绕行三十里。”众人正欲启程,忽闻远处蹄声如雷。尘烟滚滚中驰来十余骑,皆着兵部巡防服色,为首者亮出关防令箭:“奉旨稽查私结党社、煽动民议之徒!尔等携带违禁书册,形同逆旅,即刻缴械受审!”
周玉娘怒极反笑,上前一步:“请问大人,《海国图志》何时成了禁书?《民权通义》哪一条触犯律法?若读书识字便是结党,天下九成百姓都该入狱了!”那军官脸色铁青,挥手命兵士搜检行李。阿诗玛悄然退至庙墙角落,将一卷羊皮地图塞进香炉灰烬深处,又用裙裾扫平脚印。
争执间,忽听山坡上传来号角呜咽。百余苗民自林中涌出,肩扛竹梯、绳索、火把,领头长老拄杖高呼:“昨夜灯会占卜,祖灵示警:有黑蛇拦路,赤鸟破云。今日见你们灯笼上的‘图志会’标记,方知应验!”原来此地正是“破雾灯”发源地,百姓早已视寸光书院为启蒙恩主。官兵见势不妙,悻悻撤走。
队伍改道攀崖,七日跋涉终抵湖南辰州。此处乃长江支流水运枢纽,往北可乘船直抵汉口。岂料码头官吏竟接到密令,所有赴京举子须经“风评审查”,查验三代家谱、邻里保结、地方官印信,缺一不可。苏小荷递上文书,对方眯眼看了半晌,冷笑道:“女子特科虽开,然非常规功名,不得享驿站食宿、官船渡河之例。要想登船,每人先缴十两银子‘风险押金’。”
周玉娘气得浑身发抖,正欲理论,忽见江心驶来一艘画舫,朱栏绣幔,旌旗猎猎。船头立一青衫文士,朗声吟道:“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可是寸光来的诸位姐姐?”来者竟是江南实学会副会长戴衢亨之弟戴震川,奉兄长之命专程接应。他拱手道:“家兄已联络十三省商帮,组建‘助学漕帮’,专运各地赴考学子。此船不避风雨,不论性别,唯以答卷取人。”
众人登船,方知船上另聚二十七名女子考生,来自浙、闽、赣、皖各地。有寡妇变卖嫁妆求学十年者,有扮男装混入书院偷读三年者,更有盲女靠耳听笔录熟记四书五经。夜航江上,群星倒映波心,苏小荷倚舷独思,忽觉掌心微痒。低头看去,不知何时被塞入一张纸条,上书蝇头小楷:“东宫旧部仍在,太子遗诏藏于武当金殿铜龟腹中。欲知详情,三日后黄鹤楼见??李。”
她猛地抬头,只见船尾一名扫舱仆役迅速转身,斗笠遮面,身形瘦削。待追去时,人已消失在货舱阴影里。整夜她未曾合眼,反复摩挲那张字条,脑中浮现纪晓岚密信末句、“您问过的那个问题”,以及太子临终仍牵挂云南孩童读书的执念。若真有遗诏,内容会是什么?为何藏于道观而非宫廷?李德全是否尚在人间?
三日后船泊武昌,众人佯作游赏黄鹤楼。苏小荷借故离队,独自登上顶层阁楼。暮色苍茫,长江如练。忽觉身后气息微动,转头见那扫舱仆役静静伫立,摘下斗笠??竟是女子,约莫三十许,眉目清峻,左颊一道浅疤。“我是李德全义女李素筠,”她低声道,“父亲临死前说,若有人能点亮千里灯火,便可托付遗命。”
她从怀中取出一枚青铜钥匙:“武当山紫霄宫后山,有座废弃药王殿。殿前铜龟口中含珠,珠内藏诏。但切记,诏书只许三人共阅,否则触发机关,焚毁全文。”苏小荷急问:“为何选我?”李素筠苦笑:“因为您教出来的学生,在京城茶馆讲‘权利非天赐’时,太子隔着帘子听了整整一个时辰,泪湿重襟。”
当晚,苏小荷说服周玉娘与阿诗玛秘密折返武当。戴震川知情后慨然相助,调拨快船逆汉水而上。七日后抵均州,三人换作采药人装扮,在当地“图志会”成员引领下潜入深山。药王殿荒芜已久,蛛网密布,唯有那只铜龟栩栩如生,龟甲刻着八卦纹路。苏小荷颤抖着手插入钥匙,轻旋三圈,龟口缓缓吐出一颗hollow玉珠。
剖开玉珠,内藏一卷极薄蚕丝帛书。三人就着月光展读,顿觉气血翻涌。遗诏全文不足三百字,核心竟是一份“新政纲要”:
一、废除贱籍,解放乐户、惰民、丐户身份;
二、推行“普选乡议会”,每百户公推代表议决水利、赋税、教育事宜;
三、设立“实业院”,招募民间工匠研制蒸汽机、铸铁轨、造轮船;
四、开放海禁,准许沿海百姓持证出洋贸易;
五、最重要者??“朕观历代兴亡,皆始于蔽塞民智。自明年始,凡六岁以上儿童,无论贫富性别,皆须入学识字,经费由盐税提成支付”。
末尾朱批:“此策若行,大清可延百年之运;若不行,则朕之后,乱必起于东南,祸及子孙。”
三人跪地良久,泪落如雨。阿诗玛忽然道:“这不是遗诏,这是战书。”周玉娘咬牙切齿:“难怪他们要灭灯、断路、设卡??原来怕的从来不是我们考试,而是怕这份纲要见天日!”
归途中,苏小荷反复思索遗诏第五条。六年义务教育?盐税养学?这不正是她们苦苦追求的“全民识字运动”制度化吗?若能公开此诏,何愁“女子特科”不能扩招?何愁“民意箱”不能升级为议会?可一旦曝光,朝廷必称伪造,参与者皆诛九族。两难之际,她取出随身《公民手册》,翻到扉页,看见苏芸亲笔题赠:“真正的变革,不在宫墙之内,而在千万人心之中。”
她忽然明白了。
抵达北京当日,礼部贡院外已是人山人海。各省考生云集,其中女子近百,皆着素色?衫,胸前绣一朵木棉花??这是“实学联盟”统一标识。守卫士兵虎视眈眈,查验格外严苛。轮到阿诗玛时,主考官故意刁难:“彝人也算华夏子民?你的籍贯写‘云南路南州’还是‘化外蛮地’?”阿诗玛昂首答:“我的祖先在滇池畔耕读千年时,大人您的祖上还在给蒙古人牵马。”全场哗然,继而爆发出喝彩声。
考场设在国子监明伦堂,试题密封开启那一刻,所有人屏息凝神。第一场《论治国以何为本》,第二场《议边疆屯垦利弊》,第三场策问赫然写着:“若海外诸国皆行‘议会制’,民选官员共理国事,此法可施于中国否?试陈其利弊。”
苏小荷握笔的手微微发抖。这是陷阱还是契机?明知保守派必视议会为洪水猛兽,可若回避本质问题,又如何推动变革?她深吸一口气,提笔写道:“臣闻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万民之天下。昔者尧舜禅让,即是最早议会……今英吉利、法兰西虽远在西洋,然其民能议政、讼能自理、工能创新,皆因权力分散,上下相通。反观我朝,九卿闭门决策,百姓跪听宣谕,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周玉娘则另辟蹊径,引《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论证“议会非舶来品,实乃孔孟之道极致”。阿诗玛结合彝族“长老合议制”,指出西南少数民族早有民主传统,不应以“夷狄”之名排斥良政。
三日考毕,试卷封存上呈。等待放榜期间,三人并未闲坐。她们联合其他进步考生,在城南创办“夜光书院”,每晚免费讲授《民权通义》与科学常识。消息传出,京城市民蜂拥而至,连八旗子弟都有偷偷前来听课者。某夜讲至“水的电解实验”,一名白发老翁突然跪地痛哭:“老夫教了四十年八股,今日才知天地间还有这般学问!”
然而风暴终至。六月初七,顺天府突派衙役包围夜光书院,以“聚众妄议朝政”罪名拘捕讲师。苏小荷等人因持有特科考生身份暂免抓捕,但被告知“若再犯,取消应试资格”。当夜,她们齐聚客栈密议。周玉娘主张上书抗辩,阿诗玛建议潜回南方重组力量,苏小荷却取出太子遗诏副本,轻声道:“我们还有一张牌。”
次日清晨,五封匿名奏折同时递入军机处、都察院、翰林院、内务府及皇帝寝宫。每封皆附遗诏抄本一页,合计拼成全文。与此同时,三百份油印传单悄然散布街头巷尾,标题触目惊心:“先帝遗愿,今上可承?”更有人将诏书内容编成莲花落,在鼓楼前日夜弹唱。
朝野震动。乾隆连续七日未上朝,宫中传出消息:皇帝昼夜翻阅云南送来的《基层议事报告》,尤其关注其中一份关于“妇女联合抗旱”的案例??某村十六名寡妇自行组织挖渠,救活三百亩稻田,事后却被里正夺功。报告结尾写着:“她们不要奖赏,只求在村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六月十九,圣旨下达:女子特科录取名单提前公布。全国五十名额中,寸光书院占其六,苏小荷名列榜首,周玉娘第四,阿诗玛第八。其余四十二人多为官宦之女或江南才媛。旨意特别注明:“文学侍诏”衔可参与编修《天下农政全书》,并允许列席每月一次的“经筵议政”。
看似妥协,实则突破。苏小荷接旨时,当众跪拜谢恩,起身却朗声道:“谢陛下开一时之恩典,更盼万世之公器。今日我们能编书,明日就要参政;能旁听,就要主讲;能写字,就要立法!”围观人群鸦雀无声,继而爆发出雷鸣般掌声。
七月流火,新科“文学侍诏”集体赴任。苏小荷被派往工部水利司协助修订《河防一览》,周玉娘入翰林院整理历代女学者著作,阿诗玛则奉命调查西南铜矿产量虚报案。她们每日下班必聚首,将官府内部数据悄悄抄录,汇编成《实情录》秘密传回各地联络站。
中秋之夜,苏芸在书院收到最新一期《实情录》,封面绘着一盏破云而出的灯笼。她翻开第一页,见苏小荷笔迹写道:“母亲,我们已进入机器内部。这里的齿轮比想象中更锈蚀,但也更易断裂。昨日我在档案库发现,三十年来云南上报的铜产量仅为实际开采量的三成,余者尽入权贵私囊。若以此款兴学,足可建三千所夜校……”
窗外,今年的第一盏元宵灯悄然点亮。苏芸提笔,在日记本写下:“种子已经入土,根系正在蔓延。他们以为给我们一个虚衔便是恩赐,殊不知我们正借他们的笔墨,书写他们的终结。”
远处山峦叠嶂,星光如雨。某座村庄的祠堂里,一群孩子正围坐在油灯下,由一位白发老妪领读:“权利非天赐,乃众人争得之物。”稚嫩的声音穿透夜幕,飘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