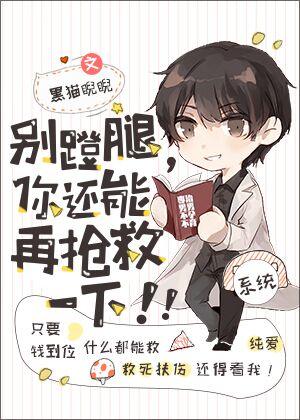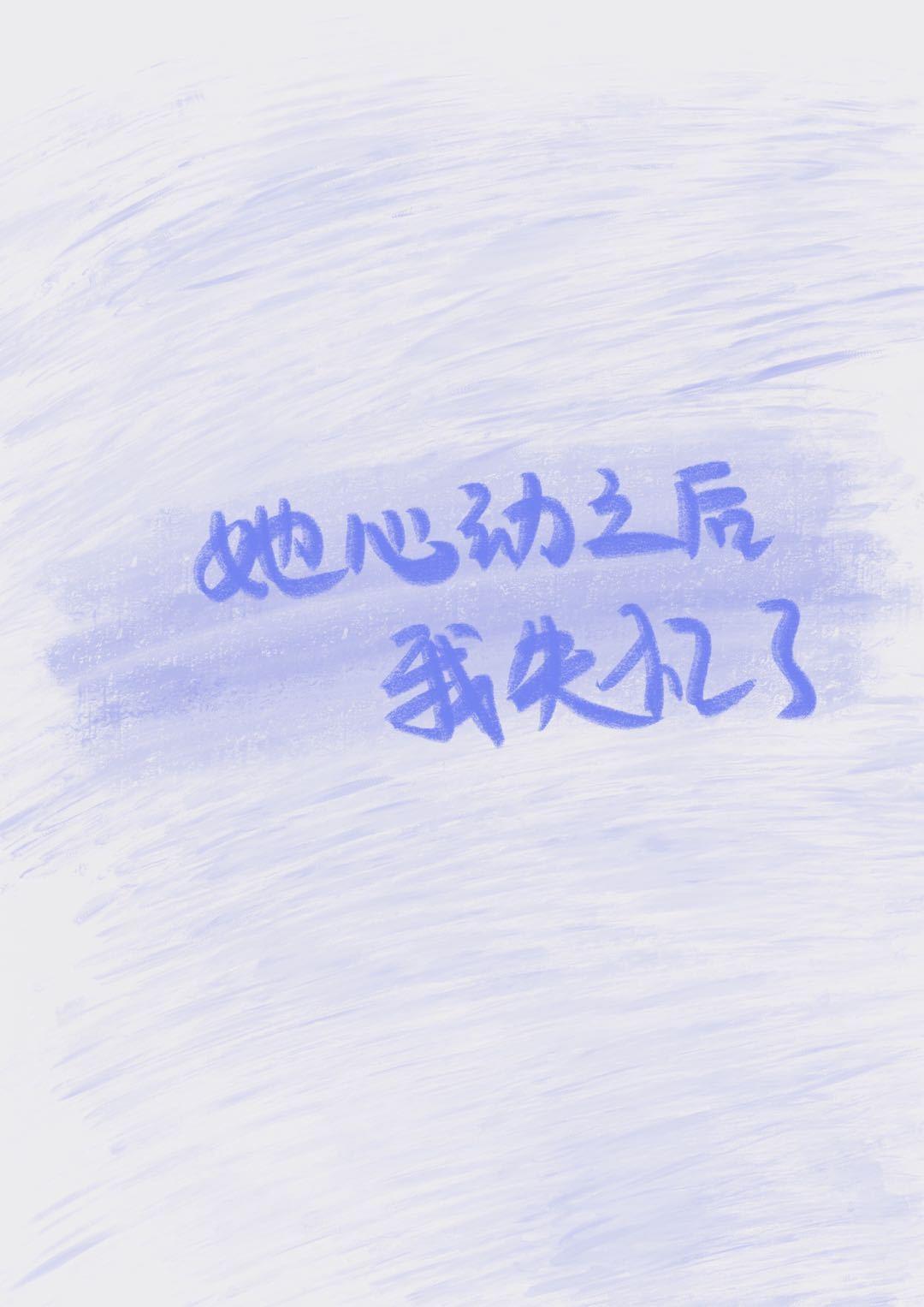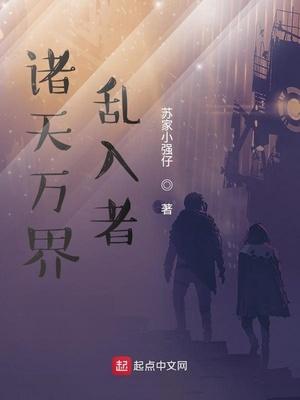笔趣阁>剑走偏锋的大明 > 第九百七十五章(第1页)
第九百七十五章(第1页)
“而我们不能拿不到真实的数据,不仅仅是因为层层盘剥,更是因为我们无力清查。”陈循道:“人不说,光是每次下乡的纸张笔墨花费,你们知道有多少?”
“于阁老总说大明官吏冗员,他没说错,在中层和上层,的。。。
春雷未动,细雨先至。江南的三月,柳絮如雪,飘在绍兴八字桥头那盏蓝灯笼下。苏小荷??如今的“沈先生”??正伏案批改学生的算题簿。烛火摇曳,映着她脸上那道从眉骨斜划至耳畔的疤痕,像一道封印,也像一枚勋章。窗外雨声淅沥,屋内却灯火通明,十几个孩子围坐在几张拼凑的木桌旁,低头演算一道新题:“某县年收粮八万石,实存仓仅五万二千石,余者何去?请列账目推演。”
一个小男孩突然抬头:“先生,是不是有人贪了?”
苏小荷不答,只微笑点头。她知道,这孩子已能从数字中看见人世的阴影。
次日清晨,义塾门前来了个穿青布长衫的陌生人,自称是杭州府学政派来的巡查员。他翻看教材,眉头微皱:“《小学详解》?此书非官定课本,何以授之?”
“回大人,”苏小荷拱手,“此书由金陵善书局刊行,内容合乎圣训,且兼重实用算术,故借用于启蒙。”
那人冷笑:“金陵善书局?就是那个印‘伪经’的地方?”
话音未落,门外忽传来一阵喧哗。一群百姓簇拥着几位乡老进来,其中一人捧着一卷黄纸:“沈先生!我们按您教的法子查了族田账册,果然发现三十年来每年少报三成租入!这是证据,我们要告到府衙去!”
巡查员脸色骤变,再不多言,匆匆离去。
三日后,省城传来消息:学政下令查封义塾,理由是“私设学堂,传播异说”。然而命令尚未执行,杭州、嘉兴、湖州三地十七所私塾竟联名上书,称“绍兴义塾教学严谨,童子明理知数,实为楷模”,请求保留。更有数十名家长自发聚集府衙门前,手持学生所制的“灾情调配图”复印件,高呼:“我们要孩子识字!要孩子明白账!”
巡抚不得已暂缓查封,只派员暗访。结果回报:“义塾所授,皆为算术、识字、读经,并无悖逆之语。”
巡抚沉吟良久,提笔批道:“若真能教孩童知廉耻、明得失,纵非官学,亦胜于空谈八股者百倍。准其续办,但不得再涉政务。”
苏小荷读罢批文,轻笑出声。她知道,禁令越软,火种越旺。当晚,她召集骨干学生,宣布成立“少年议社”:每五人一组,每月选定一村一题,调研后撰写《民情简报》,匿名投递县衙与书院。第一期主题是“孤寡老人冬衣配给不均”,第二期则是“河道疏浚款挪用疑云”。短短两月,竟有三县因此调整政策。
而此时,南京雨花台的地下密室中,周玉娘正盯着新一批即将出厂的书籍。她将一本《女诫注解》递给阿诗玛:“你看这页。”翻开处,表面是“妇德当柔顺”,下方小字却写着:“然天下女子,皆可入学读书,参议家事,乃至治国。若有才智,何分男女?”
阿诗玛低声念完,眼眶微红:“姐姐,我们真的能让女人也站起来吗?”
“已经站起来了。”周玉娘指着桌上一封密信,“苏州一位寡妇,靠卖绣品攒钱办女塾,用的就是我们印的《闺中学程》。她说,她的女儿将来要考‘议事官’。”
就在此时,一名灰衣僧人匆匆入内,带来北方急讯:格日勒的商队在归途中遭清军截击,三百册《光明书》被焚,两名随从被捕。格日勒本人跳崖逃生,现藏身于外蒙古某喇嘛庙。更令人震惊的是,漠北七旗已有五旗成立了“评议会”,并联合发布《牧民政约》,明确提出“赋役须公议,首领可罢免”。朝廷震怒,已调三千骑兵准备镇压。
周玉娘听罢,久久不语。良久,她取出一只铜盒,打开后是一叠从未启用的密电码本,封面上写着《天工开物补遗》。她对阿诗玛说:“通知所有网点,启动‘火犁计划’。”
“火犁?”
“犁过之处,不留荒土。我们要让每一本书都成为一把刀,剖开谎言;每一间学堂都成为一座炉,炼出真金。”
与此同时,北京紫禁城内,李四儿正跪在东宫书房外等候换书。他手中捧着一套新送来的《幼学琼林补注》,内里早已被他替换为经过伪装的《公民入门》。太子近来愈发爱问问题,昨日竟拉着老师追问:“为何西洋诸国百姓可以选官,我大明却不行?”讲官吓得面如土色,连忙上报。皇帝召见大学士商议,有老臣怒斥:“必是邪书蛊惑储君!”
于是宫中开始彻查太子读物来源。李四儿心知危机将至,但他不动声色,反而在今日送书时,特意多放了一本《山海经图说》,书中夹着一页手绘地图??标注了全国八十所已接收“秘密教材”的官学位置。
当夜,他躲在值房角落,用炭条在墙上写下一句话:“灯不怕风,怕无人点。”刚写完,忽听门外脚步杂乱。几名锦衣卫闯入,厉声喝问:“李四儿可在?”
他缓缓起身,整了整衣襟,走出门去。没有挣扎,没有辩解,只是平静地说:“我随你们走,但请容我把这本《论语集解》送去东宫,明日太子要考。”
领头的校尉犹豫片刻,点头同意。李四儿走进书房,将书轻轻放在案上,在扉页留下一行小字:“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然何人教我知?”
他被押入诏狱那夜,北京城下了第一场春雨。雨水顺着砖缝渗进地牢,打湿了他的裤脚。隔壁牢房传来低低吟诵声,是个因写诗获罪的举人,正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李四儿靠着墙,闭目轻和。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出不去了,但他也清楚,有些东西,牢笼关不住。
三天后,狱卒发现他在墙上刻满了字。不是咒骂,不是求饶,而是一道道数学题:
“若一县有民万户,官吏百人,每人年耗银三十两,而百姓年均收入仅五两,试问财政是否合理?”
“若有十人共管一笔钱,九人同意即可动用,如何防止多数暴政?”
“投票时如何确保匿名且不可篡改?请设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