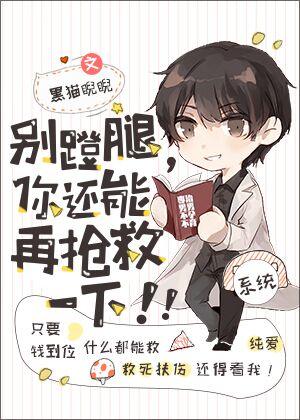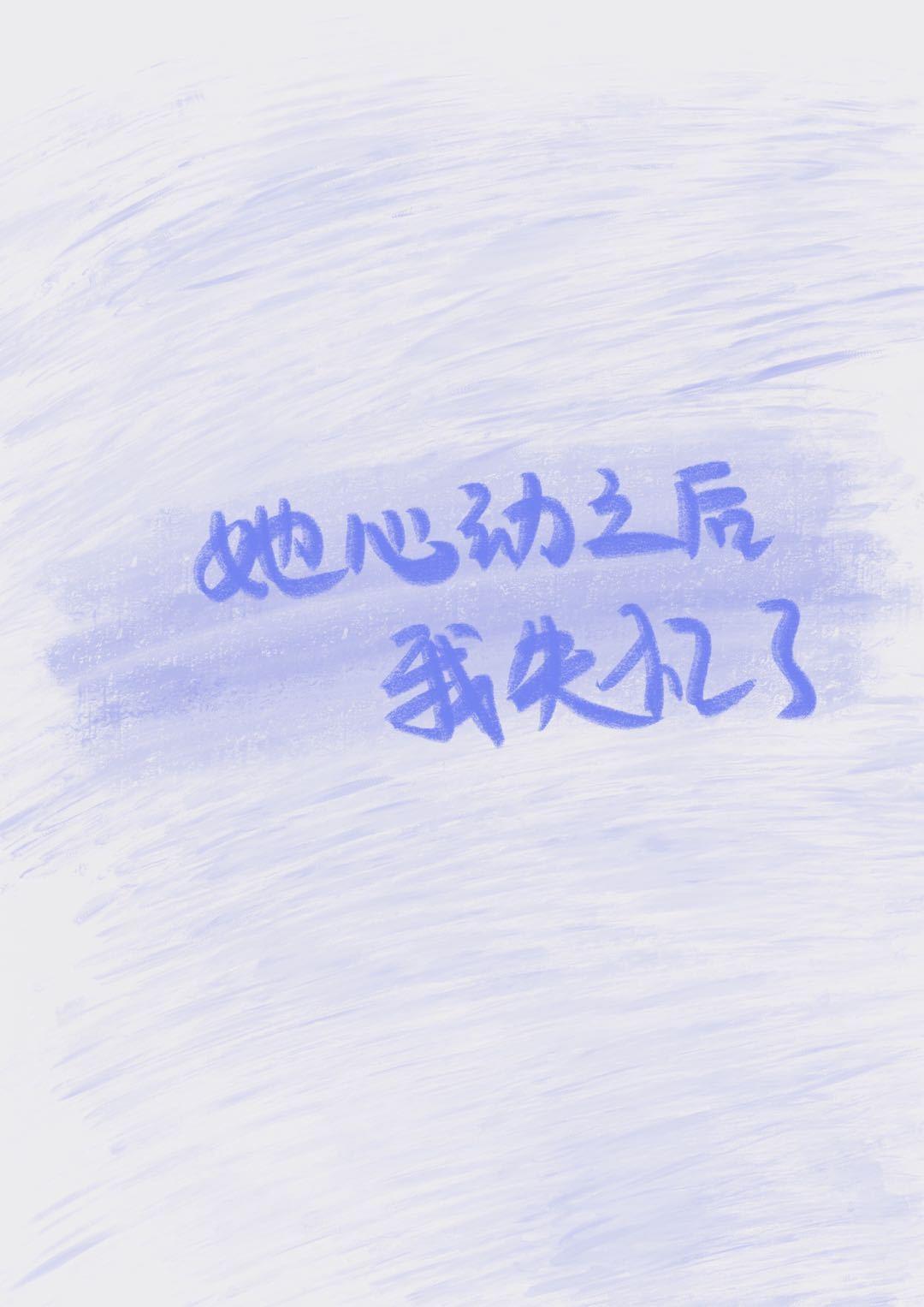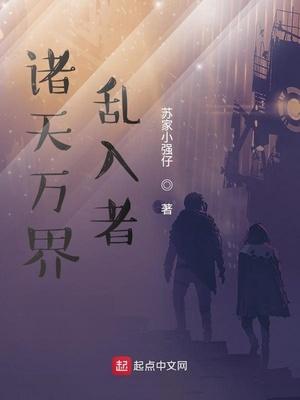笔趣阁>剑走偏锋的大明 > 第九百七十五章(第2页)
第九百七十五章(第2页)
最后一页,写着一句话:“此狱即学堂,吾辈皆考生。答案不在纸上,在千万人心中。”
消息不知怎的传了出去。京城几所书院的学生竟集体罢课,请愿要求释放“启蒙太监”。更有大胆者在校墙上书写:“李四儿不死,真理不灭。”
嘉庆帝闻之大怒,欲严惩,却被军机大臣劝阻:“陛下,杀一人易,灭众口难。今民间风气已变,童子皆习算法,妇人亦论政事,若再兴大狱,恐激成大变。”
皇帝沉默良久,终叹道:“朕治天下,原为安民。如今民自求明,岂非美事?罢了,赦其死罪,贬为边军杂役,永不录用。”
李四儿被押出京城那日,无人相送。但他走过正阳门时,忽见路边几个孩童蹲在地上,用树枝写着什么。走近一看,竟是他曾在狱中刻下的那道题。一个七八岁的女孩抬头问他:“大叔,这题怎么解?”
他蹲下身,捡起一根树枝,轻轻画了个表格:“我们先列出每个人的实际负担……”
讲完后,女孩恍然大悟:“原来官老爷花的钱,是我们一百个人的命!”
李四儿笑了,那是他入狱以来第一次笑。他摸了摸孩子的头,轻声道:“记住,数字不说谎,说谎的是人。只要你肯算,真相就在眼前。”
他被发配至甘肃凉州,充作军营文书。本以为从此沉寂,却不料当地驻军中竟有不少识字兵勇,早通过“善书局”流出的《兵民须知》了解过“权利”二字。他们听说来了个“敢教太子反问皇上”的太监,纷纷前来求教。李四儿便在军营角落设了个“夜课棚”,每晚讲一节《算术与公平》。渐渐地,连低级军官也开始旁听。有人提出疑问:“我们戍边十年,饷银常被克扣,能否用你说的方法查账?”
“当然可以。”李四儿拿出纸笔,“我们先统计应发多少,实收多少,差额流向何处……”
三个月后,这支边军竟自行整理出一份《军需弊案录》,联名上报总督。虽未立即见效,但消息传出,西北十二营陆续兴起“算账风”,士兵不再只知砍杀,更学会用笔杆子护权益。
而在南方,苏小荷的“少年议社”已扩展至浙东三十村。孩子们不仅监督赈灾、揭露贪腐,甚至开始尝试组织“模拟乡议会”。他们在祠堂摆上圆桌,每村推选一名代表,就“修桥经费如何分摊”进行辩论。有人主张按田亩出钱,有人提议富户多担,争论激烈,最终投票表决。苏小荷坐在角落记录过程,心中欣慰:这些孩子,正在亲手重建一种新的秩序。
这一年秋,浙江乡试放榜,一名来自绍兴的年轻考生高中解元。他的策论题目是《论算学致治》,文中引用大量实地调查数据,论证“清丈土地、公开预算、百姓监督”乃根除贪腐之本,并明确提出设立“地方议事厅”的构想。主考官惊骇之余,亦不得不承认:“此文虽狂,却有据有理,难以驳倒。”
榜单贴出后,全城轰动。人们打听这位解元师从何人,得知他曾就读于八字桥义塾,一时之间,各地家长争相送子前来求学。苏小荷不得不扩建校舍,增设课程,甚至邀请戴震川前来讲授“法律基础”。
戴震川来时,带了一个惊人消息:苏南某县知县,竟主动邀请“少年议社”成员参与年终财政审议。他说:“既然孩子们能算清粮账,为何不能听听他们的意见?”
那一日,十个穿着短褂的孩子坐在县衙大堂,与官员同席讨论明年修路预算。百姓围观,无不感慨:“这才是真正的朗朗乾坤。”
然而风暴始终未曾远离。
冬月初七,南京“金陵善书局”突遭查封。官兵搜出地下室印刷机,当场逮捕周玉娘与阿诗玛。审讯中,御史厉声质问:“尔等私印邪书,煽动愚民,可知罪?”
周玉娘昂首答道:“我印的是《弟子规》《千字文》,何来邪书?若说我教人识字明理便是煽动,那孔圣人岂非最大逆犯?”
对方语塞,只得暂押候审。
消息传开,江南震动。苏州、扬州、常州等地书生纷纷罢考抗议,打出横幅:“要文字狱,还是要文明?”更有数百名妇女联名上书,称“周氏教我识字,救我脱盲,恩同再造”,请求赦免。连一些致仕老臣也发声:“昔王阳明讲学,亦曾被谤为乱党,今日之事,何其相似!”
迫于压力,朝廷最终改判:周玉娘流放云南,阿诗玛罚役三年,书局关闭,设备充公。但讽刺的是,就在判决下达当日,大理寺档案库意外失火,所有涉案书册记录化为灰烬。而此后数月,西南各省市集上竟陆续出现新版《劝农吟》,封面不同,内容更精,传言出自“无名山人”。
草原之上,格日勒伤愈归来。她带回一部口述版《光明书》录音竹简,由喇嘛逐段刻录,供各旗传抄。更令人振奋的是,漠北评议会已推选出首位平民代表赴京请愿,要求承认其自治权。他们不带刀兵,只携账本与民意书,步行千里,沿途宣讲“协商政治”。所到之处,百姓焚香相迎,称其为“行走的宪法”。
而在北京皇宫深处,一位小太监悄悄将一本《小学详解》藏入皇子寝殿。他不知道是谁放的,也不知道它将影响多少未来君王的心智。他只知道,自从李四儿走后,宫里的夜晚变得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小宦官聚在一起,低声讨论“什么是公平”,“为什么百姓不能说话”。
春天再次来临。
在江西一个偏僻山村,一群农民围着一块木板,上面贴着全村收支明细表。会计是个十六岁的少年,戴着一副粗框眼镜,认真讲解:“去年卖茶收入三千二百两,修路支出八百两,结余两千四百两,全部存入公匣,钥匙由三家轮管。”
老村长拄着拐杖感叹:“以前都是族长说了算,哪知道还能这样活?”
年轻人笑着说:“沈先生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远处山坡上,一位旅人停下脚步,望着这片宁静村落。他从怀中取出一张地图,正是当年李四儿刻在狱墙上的那份全国“秘密学堂”分布图。如今,红线已连成网络,覆盖十八省,三百余点。他轻轻抚摸纸面,喃喃道:“火犁已过,沃野千里。”
风拂过麦田,掀起层层绿浪。
谁也没有注意到,田埂边一朵野菊悄然绽放,花瓣如星,灿若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