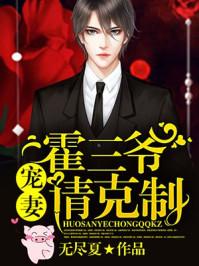笔趣阁>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596章 真正的绝境降临了(第3页)
第1596章 真正的绝境降临了(第3页)
>**“很好。因为你们都在听。”**
她睁开眼,望向星空。
一颗流星划破天际,坠入远方湖心,激起一圈圈涟漪。
而在湖底,一朵由虹彩结晶构成的花,正悄然绽放,花瓣舒展之际,释放出一段绵延千里的频率波,穿越地壳、海洋、大气,最终融入地球神经系统的每一次搏动。
这频率没有名字,也不需要翻译。
它只是存在着,像呼吸一样自然,像爱一样恒久。
多年以后,一位哲学家在著作《倾听时代》中写道:
>“我们曾以为文明的进步在于说得更多、更快、更强。
>可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人类第一次选择沉默的那一刻。
>那一天,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教会我们:
>最深刻的语言,从来不是说出来的。
>而是当你停下所有声音,依然能感受到的??
>那份来自世界的、轻轻的回响。”
书末附录中,记录了一则民间流传甚广的童谣,据说源自某个偏远山村的孩童游戏,歌词简单至极:
>小耳朵,竖起来,
>风在讲,花在开。
>谁不说,谁都在,
>听见你,我就来。
没人知道这首歌最早是谁唱的。
但在每一个孩子入睡的夜晚,总会有大人轻声哼起它,仿佛在传递某种古老而温柔的承诺。
而在宇宙某个角落,或许正有一双眼睛,静静望着这颗蓝色星球,看着它一点点学会倾听,学会共情,学会在喧嚣尽头找回最初的宁静。
那双眼睛不属于神明,也不属于英雄。
它属于一个曾被送上山修行的哑童,一个被派下山娶妻却震惊了世界的少年,一个最终把自己化作频率、融入万物之间的桥梁。
他没有墓碑,不需要雕像。
因为他已成为这个世界本身的一部分。
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安静下来,只为听另一个人说完一句话;
只要还有一滴眼泪因理解而非怜悯而落下;
只要还有一次拥抱,是因为“我懂”而不是“你应该”??
那么,他就仍在行走。
仍在倾听。
仍在轻声说着那句贯穿一生的告白:
>**“我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