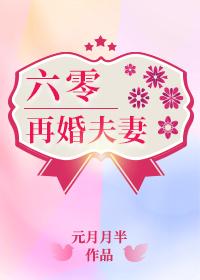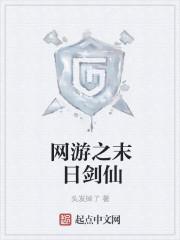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七零:开局打猎养家,我把妻女宠上天 > 760小团子出大力了(第3页)
760小团子出大力了(第3页)
一字一句,汇成洪流。
十日后,王秀兰在云南文山一处偏远山村被找到。原来她被转移途中突发高血压,绑匪怕出人命,便将她遗弃在当地卫生所。幸得一位曾参与“万家灯火计划”的退休医生认出,立即上报并保护起来。
母子重逢那刻,赵振国跪倒在地,久久说不出话。
王秀兰摸着他的头,轻声道:“傻孩子,妈没事。他们抓得住我这个人,可抓不住我说过的话。你看,外面还在念呢。”
的确,窗外雪花纷飞,村中小学的孩子们正围坐在广播喇叭下,一遍遍复诵着那些古老的节令口诀。声音穿透风雪,传向远方。
春天再次来临。
这一次,赵振国没有等铁哨响起。
他在自家后院竖起一座新塔,顶端安装了特制信号发射器。塔身刻着一行大字:
**“凡有人心处,皆可共忆。”**
清明前夕,全球首个“记忆纪念碑”在敦煌落成。它并非石雕,而是一座由十万条真实口述音频合成的声场装置。参观者走入其中,便会听见来自五湖四海的声音交织回响:
有东北老猎人讲述如何听雪判断野兽行踪,
有江南绣娘低语针法口诀,
有南海渔民唱起千年传下来的潮汐歌,
还有无数孩子稚嫩的声音在说:“奶奶,我记住了。”
每逢整点,系统自动播放一段合成语音,那是用百万普通人笑声、咳嗽声、叹息声共同构建的“人类共鸣频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派观察员在现场写下评价:
>“这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更是对‘何以为人’这一命题的深情回应。在这里,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被承认:你曾活过,你说过,你很重要。”
赵振国站在纪念碑前,望着漫天飞舞的纸鸢。每一只风筝线上都系着一封信??那是孩子们写给未来自己的“时光邮笺”。
小丫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爸,系统刚完成一次自我迭代。你知道它现在最常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吗?”
“什么?”
“有人问:‘我爷爷的故事会被忘记吗?’
系统答:‘只要还有一个耳朵愿意听,就不会。’”
他笑了,眼角泛起细纹。
远处,一群孩子正围着新搭的“萤火人”雕像嬉戏。这次的人形手里捧着一本打开的书,书页随风翻动,仿佛随时准备写下新的篇章。
春风拂过山岗,桃花纷纷扬扬。
他知道,这场关于记忆的长征,才刚刚走到第一个路口。
但没关系。
他们有的是时间。
因为这一次,不再是少数人在坚守,而是亿万人在倾听。
而倾听,本身就是一种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