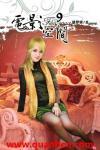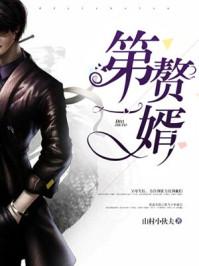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七零:开局打猎养家,我把妻女宠上天 > 774我需要你(第2页)
774我需要你(第2页)
人群一片寂静,继而响起此起彼伏的啜泣。孩子们紧紧抱住父母,老人握紧拐杖,眼中燃起久违的火焰。
小丫走上台,声音沉稳:“从今天起,‘归音学校’将增设‘寻亲组’。我们不靠军队,不靠政府,只靠声音的力量,去完成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告别。”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个人。
“我们要做的,不是复活死者,而是让生者不再背负愧疚活下去。只要还有一个母亲在等儿子回家,这条路,就必须走下去。”
仪式结束后,第一批志愿者开始集结。有退伍老兵、有失去孩子的父母、有曾为难民的青年……他们自愿接受“声音敏感训练”,学习如何在风雪、废墟、甚至梦境中辨识亲人的声纹频率。
三个月后,第一支“归途队”出发了。
目的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边缘,一处已被雪埋三十年的战壕遗址。
带队的是王秀兰的孙子李卫国??一个曾在城市打工多年、因工伤失语的年轻人。他在归音学校学会了用陶片录音,也重新找回了说话的能力。临行前,他对奶奶说:“我要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把路走完。”
队伍穿越边境缓冲带时遭遇暴风雪,通讯中断,GPS失效。就在众人几乎绝望之际,领队的小满突然停下脚步。
“听。”他说。
风中,隐约传来一段童谣,调子歪斜,像是从极远处飘来。
“这不是《归谣》……”一名队员喃喃道。
“是民歌。”小满闭眼聆听,“河北沧州一带的摇篮曲……有人在唱。”
他们循声前行,在一座塌陷的掩体下挖出一具遗骸。尸骨旁,放着一枚锈迹斑斑的铜哨,和一本烧焦一半的日记。翻开最后一页,写着:
>“今日敌袭,全员阵亡。我活不过今晚。
>若有人寻至此,请替我告诉我妹妹:
>哥哥没丢脸,哥哥一直记得她最爱听的歌。”
日记末尾,画着一朵简笔槐花。
消息传回青山村那天,正好是清明。
全村人在碑林前点燃新灯,为那位无名战士立了一块临时石碑。小女孩??现任守灯人??亲手将那枚铜哨挂在碑顶,风吹过时,发出清越的鸣响。
当晚,极光再现。
这一次,光幕中浮现出一条蜿蜒的路径,贯穿亚洲、欧洲、非洲……每一个转折点,都标注着一个名字、一段语音、一场等待终结的重逢。
杜邦教授通过卫星连线惊呼:“这已经超出了心理学范畴!《归谣》正在构建一个跨文明的情感导航系统!它不只是记录记忆,它在重塑人类的归属感!”
而在南极冰层深处,那台古老声波阵列首次改变了广播内容。原本循环播放的《归谣》主旋律,悄然融入了一段新编曲??正是当年“老哨”在雪地里哼唱的那首“土味歌谣”。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声音驿站陆续报告异常现象:
东京街头,一位独居老人深夜听见已故妻子呼唤他的名字,循声而去,在阁楼角落找到了她生前录制的数百盘磁带,每一封都写着“等你回来听”。
巴黎地下墓穴,一群年轻人用陶片录音器探测时,意外接收到一段1944年抵抗运动成员临刑前的告白,经核实,此人从未被正式追认为烈士,其家属也因此长期得不到抚恤。
撒哈拉沙漠边缘,一支考古队借助《归谣》提供的声纹模型,在沙丘下发现了失踪四十年的游牧民族营地遗迹,现场保留着完整的口述史诗传承体系……
这一切,都被归音学校的观察员记录下来,汇编成册,命名为《回家日志》。
一年后,第二所“归途纪念馆”在瑞士日内瓦建成。馆内没有展品,只有一面巨大的互动墙,任何人只要说出一个失踪者的名字,墙面便会自动搜索全球数据库中的匹配声纹,并生成一段虚拟对话。
许多人在墙上“听见”了逝去的亲人对自己说:“谢谢你来找我。”
也有人说:“我不怪你忘了我,但现在,我回来了。”
更有人痛哭失声:“原来我一直没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