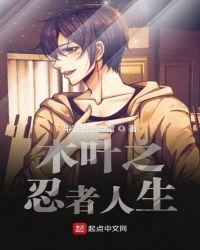笔趣阁>旧日音乐家 > 第二十四章 夜行漫记其一 会众(第2页)
第二十四章 夜行漫记其一 会众(第2页)
范宁迈出一步,踏入新生的湖泊。
水没过脚踝,却没有寒冷,反而传来一种熟悉的温暖,像是母亲的手抚过额头。他抬起右手,轻轻拨动吉他的一根弦。
没有声音。
但在所有人(包括影子)的意识中,响起了一声钟鸣。
那是圣礼堂的钟声,是学校放学的铃声,是剧院开幕前最后一声调试麦克风的嗡鸣。
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却存在于每一个与艺术相遇的瞬间。
随着这一声钟响,湖面上的倒影开始流动。
画面切换:
??巴黎左岸的小酒馆里,一名女歌手抱着破旧吉他吟唱,台下只有一个听众,正低头写着什么;
??西伯利亚的铁路车厢中,一位老兵用口琴吹奏民谣,雪花从车顶缝隙飘落,落在他冻伤的手指上;
??东京某间地下排练室,四个少年在暴雨夜完成最后一遍排练,主唱撕心裂肺地唱完最后一个高音后瘫倒在地,鼓手笑着哭了;
??南极科考站的休息室,科学家们围坐在一台老式唱片机旁,听着肖邦的夜曲,窗外极光如帷幕般垂落……
每一幕都短暂得如同眨眼,却又深刻得像刻入骨髓的记忆。
而每当一幕结束,便有一道新的影子从湖水中升起,加入范宁的行列。
它们不再模糊,不再残缺,而是清晰得能看清衣领上的褶皱、眼角的细纹、袖口磨损的线头。
“你看到了吗?”范宁对着虚空问道。
“看到了。”是安德烈的声音。
少年不知何时已站在湖畔,浑身湿透,怀里紧紧抱着一把儿童尺寸的小提琴。他的眼睛亮得惊人,像是燃烧着两簇看不见的火焰。
“我本来不信的……我以为那只是一次偶然的对话,一场梦。可是现在,我听见了!那些我没听过的声音,那些本该属于我的旋律……它们一直在等我!”
范宁转过身,看着这个曾在他面前迷茫发问的少年。
“那你现在明白了吗?艺术不是答案,它是提问的方式。我们演奏、绘画、写作,并非为了终结疑问,而是为了让疑问活得更久,传得更远。”
安德烈重重点头,泪水混着湖水滑下面颊。
“我想学,我想成为那个……传递问题的人。”
范宁伸出手,从灯腔中取出另一粒微光闪烁的尘埃,递向他。
“这不是天赋,也不是恩赐。它是责任。接受它,意味着你将再也无法假装无知,再也无法对世界的沉默保持沉默。”
安德烈没有犹豫,伸手接过。
尘埃融入掌心的刹那,他的瞳孔闪过一道银光,仿佛有千万段乐谱在脑海中同时展开。他踉跄一步,几乎跌倒,却被一道无形的力量托住??那是来自身后众多影子的共鸣,是跨越时空的扶持。
“欢迎归来。”范宁轻声道。
此时,湖面已扩展至整个视野所能及之处。
水中的倒影不再局限于过去,也开始映照出未来:
??一座漂浮在云层之上的音乐学院,学生们在无重力环境中演奏交响乐;
??火星殖民地的夜晚,一位盲人用触觉乐器演奏地球古调,听众是戴着翻译芯片的异星访客;
??深海城市的核心,巨型生物与人类共同谱写一部以洋流为节拍、鲸歌为和声的史诗……
“夜行漫记”进入了终章。
弦乐群奏出宽广的主题,如同黎明推开黑夜的大门;铜管以克制的力度加入,象征秩序与希望的重建;打击乐则隐于背景,模拟心跳,模拟雨滴,模拟所有细微却恒久的存在。
范宁再次拨动琴弦。
这一次,声音真实地响起了。
是一段简单的旋律,只有五个音符,却蕴含着无限变奏的可能性。它像种子落入土壤,迅速生根发芽,被风带走,被水流传播,被每一个影子铭记。
湖床上的光越来越强,直至淹没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