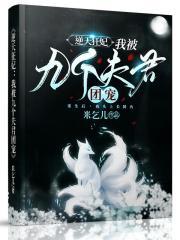笔趣阁>我真没想下围棋啊! > 第四百九十九章 他在支撑着我(第1页)
第四百九十九章 他在支撑着我(第1页)
“这里没有尖,而是??”
“大跳了?!”
所有人都被突如其来的一手惊到了。
本来他们想的都是黑棋尖,白棋长,黑棋挖,白棋挡,结果黑棋这里没有尖,而是突兀一手大跳,顿时打断了所有人的思。。。
车子驶出怒江峡谷,沿途的山势逐渐平缓,红土裸露的坡地被成片的油菜花田取代。阳光斜照在金黄的花海上,泛起一层流动的光晕。我靠在车窗边,手里仍攥着普路那封信,信纸边缘已被汗水微微浸软。沈砚之坐在副驾,闭目养神,手指却始终搭在背包外侧??那副围棋盘还在,仿佛成了我们之间某种无声的契约。
“你说他以后真能飞出去吗?”我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沈砚之没睁眼,只轻轻“嗯”了一声:“他已经起飞了。只是别人还没看见。”
我低头翻开《第十八本》日记的复印件,那是临走前普路悄悄塞给我的。最后一页写着:
>“今天我把‘白子陪伴’刻在了窗框朝南的那一面。
>如果明年春天有燕子来筑巢,我就写一首诗送给它们。
>诗的名字叫《会飞的棋子》。”
字迹比从前工整,却多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快,像是从沉重的壳里挣脱出来的呼吸。
手机震动起来,是杨老师发来的消息:“普路今早去学校了,坐在教室第一排。他妹妹说,他昨晚写了整整一夜,准备交第一篇作文。”
我笑了,把手机递给沈砚之。他看了一眼,嘴角微扬,终于睁开眼,望向远方的地平线:“下一站,临夏。”
---
甘肃临夏,东乡族自治县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藏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里。这里风大,尘土常年弥漫在空中,像一层薄纱罩住整个小镇。校门口立着一块斑驳的石碑,上面刻着“光明之家”四个字,漆色剥落,却依旧清晰。
接待我们的是位年近六十的回族妇女,名叫马阿娘。她穿着素净的黑袍,头巾下露出一双温和而疲惫的眼睛。“你们来得正好,”她说,“再过三天就是‘心音节’,孩子们要演出。”
“心音节?”
“是我们自己定的日子。”她笑了笑,“这些孩子看不见光,但他们记得声音的模样。每年这一天,他们用耳朵里的世界编一支歌,唱给彼此听。”
她带我们走进一间低矮的砖房,门一推开,一股暖意扑面而来。屋内坐着七八个盲童,年龄从八岁到十五岁不等,全都安静地围坐一圈,手中握着不同材质的小物件:铃铛、木槌、陶笛、铜钹。中央坐着一个约莫十三岁的男孩,瘦削的脸颊上有一道浅浅的烫伤疤痕,正用指尖轻轻摩挲一面羊皮鼓。
“这是伊布拉,合唱团的‘指挥’。”马阿娘低声介绍。
伊布拉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到来,缓缓转过脸,嘴角扬起一丝笑意:“有人来了?”
“是两位远方的朋友。”马阿娘握住他的手,“他们听说你们在唱歌。”
“那……能不能让他们听听?”他轻声问,“我们还没练完,但我想让他们知道??黑暗也能开花。”
话音落下,屋内响起一阵??声。一个女孩摸索着拿起陶笛,吹出一段悠长的引子,像是晨风吹过山谷;紧接着,另一个男孩敲响铜钹,节奏如心跳般沉稳;伊布拉双手落在鼓面上,开始缓慢击打,每一记都像大地深处传来的回响。
然后,他们齐声唱了起来。
没有歌词,只有音节的起伏与和声的流转。有的声音清亮如溪流,有的低沉似夜风,他们在用记忆中的色彩谱曲??有人唱出了母亲煮奶茶时锅盖跳动的声音,有人说那是麦浪翻滚的节奏,还有一个小女孩坚持认为,她的旋律是“紫色的”,因为“它闻起来像薰衣草晒干后的味道”。
我闭上眼,泪水无声滑落。
这不只是音乐,是灵魂在黑暗中为自己点亮的篝火。